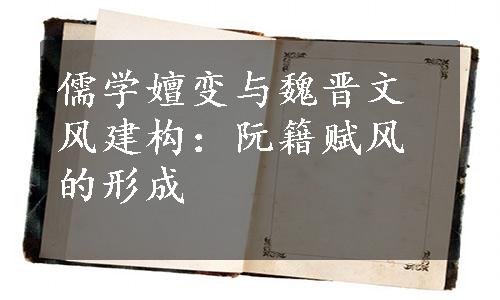
阮籍为阮瑀之子,阮瑀少学于蔡邕,可知阮籍家学有一定的儒学色彩。尽管建安十七年阮瑀死时阮籍只有三岁,受其父直接影响较少,但阮瑀留存的诗文作品同样能对阮籍起到导引作用。如《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137]伏义《与阮嗣宗书》说:“吾子雅性博古,笃意文学。积书盈房,无不烛览。目厌义藻,口饱道润。俯咏仰叹,术可纯儒。”[138]上述均表明阮籍不仅继承了阮瑀的才藻声华、儒学素养,同时又深受当下玄学思潮的浸淫。这种玄儒并参的思想面貌,又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尤其阮籍辞赋对儒典的化用、儒学价值体系的承传较之《咏怀诗》都更突显一些。因此,阮籍儒玄嬗进的思想演化过程,也是其赋风特色形成的过程。
一、阮籍创作中儒学文艺特色的渊源
阮籍幼年失怙,曹丕、王粲曾作《寡妇诗》、《寡妇文》予以哀悼,[139]艰苦的阅历使阮籍养成了城府杳深,又任达不拘的性格。他思想中杂容了儒家、道家和纵横家的因素,虽然在析辞辨理、寻绎推演方面不如何晏、王弼等人严密,但他侈丽宏衍的言说方式,直觉多于智性的论证风格,却丝毫不减何、王等人的深邃和宏阔。
高晨阳将阮籍的思想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正始之前,阮籍表现出引老入儒、以老解儒的倾向,但并没有摆脱儒学的基本思想框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乐论》、《通易论》;第二阶段为正始后期,阮籍在理论操作层面真正做到了引老入儒、以老解儒,实现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代表作是《通老论》;第三阶段为正始之后的完整意义上的“竹林之游”开展的时期,庄学的反叛品格和批判精神得到空前发扬,其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个体自我的绝对自由被倡言到极致,此间代表作是《达庄论》、《大人先生传》。[140]阮籍的思想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冲击,也赋予他诗文作品思辨性和含蓄性的特色。
刘师培从行文风格、语脉特色着眼,称阮籍文赋深受阮瑀、陈琳的影响。[141]如果推而广之,阮籍诗歌亦有明显承继前两者苍劲悲凉、忧郁哀沉等特质的痕迹。陈琳《饮马长城窟》发抒中心悲慨,可谓沉痛卓绝。另外,他的两首无名诗作较为细腻、深入表述了他的精神世界,其中“不娱”、“悲感”、“惆怅”、“嘘唏”、“慷慨”等词在前诗出现的频率颇高,诗中充满木草凋枯、日月川逝的空寂紧迫的情绪。[142]阮瑀诗歌中有着较其它建安文士更为浓烈、粘稠的抑郁悲凉的情愫,哀伤几乎成了其涂抹诗意空间的唯一色彩,其《七哀诗》、《杂诗》、《苦雨诗》均可代表。阮瑀的这些诗歌均直接揭示内心的困惑、哀戚和苦痛,如“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抒发客寄的孤独;“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抒发思乡的绵愁;“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抒发死亡的恐惧等等。[143]在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方面,陈琳高呼“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144]因此同样是抒发愁怀,陈琳佩弦自急,充满期待,而阮瑀则消极遁世,看不到希望,在自我封闭的悲情世界中越陷越深。《文士传》载其精通音律而被曹操视为“技人”,[145]而好友刘桢又因为狂悖行为遭到输作徒吏的惩戒,这些无疑都促生了其内心浓重的悲伤情臆。阮瑀缺乏必要的进取精神的驱动,或者说是某种实用生存哲学的倚赖,从而内心世界充满悲观甚至绝望的情调,这又为他先于大多数建安文士病殒提供了病理依据。阮籍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父亲忧郁的基因,但毕竟又获得时代玄风大畅的嘉惠。因此,他并未像父辈一样因为找不到现实与精神的出路自闭而终,虽然同样面临着社会人生的种种蹇困和磨难,但他的精神在充满挣扎与扭曲的同时,又保持了自由、清醒、独立的特质,这一切不止表明父子两代人时与命的显著差异,同样还标志着以本体自觉为主流的新的人文时代的开始,它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新的文风范式树立的开始。[146]这种新的文风,亦即依托个体如何遗落名教束缚而达到自然至境的思辨而呈现出的玄远之风,不仅仅是对建安文坛慷慨苍凉文风的转变,也是对黄初一味清老、正始诗杂仙心的转变。当然,从何晏《言志诗》就已初步呈现了儒家忧患意识与道家逍遥境界结合的特点,而直到阮籍、嵇康这里才可谓蔚为大国,使曹魏易代之际的文坛具有了令人瞩目的光彩。
二、阮籍早期辞赋创作中的儒风特色
与阮籍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相适应,他的作品也经历了早期以儒学为指归,中期杂糅儒道、以道解儒,后期儒道对立、以道非儒等变化,这些变化对其文风形成的作用不容轻视。阮籍于正始三年(242)被迫应太尉蒋济之命入仕,入仕前他作了一篇奏记给蒋济说:“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篲;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穷居韦带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礼下之者,为道存也。”[147]他以子夏被魏文侯礼遇、邹衍得到燕昭王重用为喻,强调蒋济有重才之“道”,但他托以足疾而拒绝,可谓有礼有节。他还有一篇奏记说:“昔荣期带索,仲尼不易其三乐;仲子守志,楚王不夺其灌园。”也表达了“毕愿家巷”的目的。[148]值得一提的是,短短的两则奏记,其所用多处儒典,如“以含一之德”,化意于《尚书·咸有一德》;子夏授学一事,则出自《礼记·檀弓上》;“负薪疲病”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孟仲子所言“昔者有王命,有负薪之忧,不能造朝”;“仲尼不易其三乐”句,出自《孔子家语·六本》;“仲子守志”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149]上述两则奏记说明,阮籍入仕之初不仅深谙儒家典籍,而且流露出对贤者退隐的仰慕。
此后,正始八年(247)阮籍又被曹爽征为参军,此时朝中的权力争夺已日趋激烈,阮籍托疾不出,至嘉平元年曹爽被诛,时人服其远识。这一段时间,何晏、荀粲、王弼等人倡导玄风,对阮籍可能有潜在影响。以荀彧之子荀粲为例,何劭作《荀粲别传》说荀粲诸兄多言儒术,而他独谈道家,并称:“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150]他的认识来自《庄子·天运》老子所言“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与《庄子·天道》轮扁所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这种观点无疑具有很强的颠覆性。他甚至评价父亲荀彧不如从兄荀攸,认为前者整肃守礼却不能善终,后者不修边幅而得自保,结果引得诸兄怒目相向。另外,他宣扬女子色重于才,与《论语·学而》“贤贤易色”的观念背道而驰。他娶曹洪女为妻,专房欢宴年余,后者病世。荀粲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151]一年后他也去世,年仅二十九岁。荀粲轻六经、忽父讳、纵女色、重情感的做法,都可以在阮籍甚至阮咸身上找到对应之处。[152]因此,嘉平四年(252)阮籍再度出仕为司马师从事中郎,其思想中儒道糅合、以道解儒的迹象愈发明显。相对来说,文学作品不同于哲学专论,它更倾向于表达感性题材,反映作者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因而也往往更接近于作者最真实的内心情态。阮籍的儒家思想、审美意趣无疑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它们在诗赋中要经历从弱化到被批判的过程,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阮籍此期赋作中的儒学倾向还比较突出。(www.daowen.com)
此间他作《鸠赋》,其序说:“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之旨,后卒为狗所杀,故为作赋。”[153]嘉平元年(249)发生高平陵之变,对正始名士而言不啻灭顶之灾,这也引起当时舆论的同情。如蜀费祎《甲乙论》特为曹爽鸣不平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154]因此,阮籍此赋具有更多的政治寓意在。[155]整首赋描述了两只幼鸠因风振落而获救直到最终丧于犬口的过程,表现出对生命殒逝的感伤。整篇赋也具有儒家仁爱观念的影子,如开篇“旷逾旬而育类,嘉七子之修容”句,即是对《诗经·曹风·鸤鸠》“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乐场面的再现,另外曹植《责躬表序》也说“七子均养者,鸤鸠之仁也”,[156]都有助于理解阮籍“鸤鸠”意象中的仁爱意蕴。因此,它们在被秋风从巢中振出之后,作者表现出“终飘遥以流离,伤弱子之悼栗”的悯怀之情。最后,鸤鸠被狗所吞,引起作者“嗟薄贱之可悼,岂有忘于须臾”的感伤,[157]其恻隐之心略见无遗。伏义称阮籍:“俯咏仰叹,术可纯儒。然开阖之节不制于礼,动静之度不羁于俗。凡咨咏,善之则教慈于父兄,恶之则言丑于仇敌。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丑其言而乐其业者也。”[158]可见,阮籍“术可纯儒”的一面得到伏义的充分认可,而《鸠赋》则是其“慈其教”的体现。
三、阮籍中期玄儒互参与思辨批判的赋风
正元元年(254),阮籍因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其中期的创作也开始了。是年秋作《首阳山赋》。此赋不同于《鸠赋》,其以感怀伯夷、叔齐的旧事为主,对群伪乱真、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对“仁义”之道也提出质疑。这篇赋不长,但布局很有特点,有一半的篇幅写游目首阳山、静立独思;另一半则感发古事,是为“遥思”的内容。因为赋的后半部分仅论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一事,并迅速作结,这就造成了欲言又止的压迫感。阮籍所关注的显然不只是伯夷、叔齐之死本身,而对周王灭商是否真正符合仁义原则提出疑问。阮籍说:“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曾投奔周文王而不得,后又谏诅武王伐纣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159]阮籍显然利用上述记载,认为“彼(即伯夷、叔齐)背殷而从昌”,本身就是叛离宗国,不值得羡慕;继而“此(即周武王)进而不合兮”,则是说周武王未尽父丧而兴兵伐君,也不符合仁义。他就消解周朝建立与伯夷、叔齐之死的崇高内涵,并对世间的“美论”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他还列举诸如“将修饰而欲往兮,众而笑人”、“怀分索之情一兮,秽群伪之射真”、“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的现象,这为他以“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作结奠定了基础。[160]这篇赋体现了他由思辨哲学批判向历史哲学批判的过渡,同时也赋予了重读历史的现实性意义。甘露三年(258),司马昭为相国,进位晋公,阮籍作《为郑冲劝晋王笺》,将司马昭比作周公,且称“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161]亦对司马懿也多有溢美之辞,对照《首阳山赋》中的批判精神,其违心之处亦可明见。[162]陈伯君引范陈本《首阳山赋》注文说:“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词隐。”[163]应该说,阮籍为了避免批判儒家圣哲及现实政治带来的祸患,而选择历史性的题材。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将愤激批判的感情压缩隐含到平静的表述中,从而造成了作品含蓄玄远的风格。
正元二年(255),阮籍为东平相,作《东平赋》。这篇赋杂入了都邑赋与游仙赋两种体裁,却没有沿袭两种各自固有的写法,从而多有新意。《东平赋》开篇部分以《尚书·禹贡》中九州观念为据,提出理想中城邑的布局:“分之国邑,树之表物,四时仪其象,阴阳畅其气,傍通回荡,有刑有德。”他在接下来对东平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人文地理的描述中,虽有客观的成分,却注入了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这又在城邑赋中绝无先例。他说:“其厄陋则有横术之场,鹿豕之墟,匪修洁之攸丽,于秽累之所如。西则仰首阿甄,傍通戚蒲,桑间濮上,淫荒所庐。三晋纵横,郑卫纷敷,豪俊凌属,徒属留居。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仍乡饮而作慝,岂待久而发诸。”又“其土田则原壤芜荒,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流潢余溏,洋溢靡之。”由此他得出不宜久居的结论:“居之则心昏,言之则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怀。”在难言的失望之余,他流露出对仁义之邦的向往:“甘丘里之旧言兮,发新诗以慰情。信严霜之未滋兮,岂丹木之再荣。《北门》悲于殷忧兮,《小弁》哀于独诚。鸥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仪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灵。”[164]应该说,他的这种情感植根于《诗经·邶风》、《小雅》、《周易·渐卦》等经典的描述,但现世中与东平相似或不如的地方实在太多,他只有寻求虚幻的仙游境界实现他对乐土的企盼,因而接下来的部分以及“重曰”又带有了游仙赋的成分。它们多以《庄子》、《山海经》、《淮南子》、《列仙传》等记载为依托,虚拟了一个“永欣欣而康乐”的精神境界。[165]这篇赋杂糅都邑赋与仙游赋两种体裁,混合儒道两种意趣,并把道家的逍遥飞升作为儒家理想难以实现的解脱方式,体现出以道解儒的理路。与之相似的还有《亢父赋》,赋中对亢父的批判一如《东平赋》中毫不留情:“人民顽嚣梼杌,下愚难化。”又“人民被害嚼啮,禽性兽情”。又“人民侧匿颇僻,隐蔽不公,怀私抱诈,爽慝是从。礼义不设,淳化匪同”[166]。体现出他对世俗民情的愤激情绪。应该说,这种情绪的儒家道德指向是非常鲜明的。
四、阮籍后期辞赋对儒学文艺观的改造与突破
体现阮籍后期哲学思想的作品,可以《清思赋》、《大人先生传》等为代表。前者似承司马相如《美人赋》、张衡《定情赋》、蔡邕《青衣赋》、杨修《神女赋》、王粲《闲邪赋》、《神女赋》、阮瑀、陈琳《止欲赋》、刘桢《清虑赋》、应玚《正情赋》、曹植《静思赋》、《洛神赋》等作而来,它们基本都倡导或受制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并在此原则下探讨情与礼的关系问题。当然,撇开先辈作品的艺术成就不论,阮籍采用道家遗形取神、澄虑玄览的思想方法,较为彻底地摆脱了人对情色的感官依赖,而上升到理性至美的思辨境界,亦即他所说的“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的状态。[167]这样就摆脱了情与礼相纠葛的命题模式,而进入情与思的新型思辨中来,也就是说他将原本儒家关注的伦理命题转化成为道家观照的思辨命题。《清思赋》基本上在谈他如何苦思而达到“忽一悟而自惊”的觉悟过程,因此篇中充满了自我意识的流动与情绪蔓延纠缠的情形,如“意流荡而改虑兮,心震动而有思。若有来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辞。心恍忽而失度,情散越而靡治。岂觉察而明真兮,诚云梦其如兹。惊奇声之异造兮,鉴殊色之在斯”,直到他感到“殊色”的存在,标志着感受到清虚境界的至美。在精神巡游的过程中,他进入昆仑、西海、瑶岸、平圃等仙境,并受到美人的服侍:“敷斯来之在室兮,乃飘忽之所晞。馨香发而外扬兮,媚颜灼以显姿。清言窃其如兰兮,辞婉婉而靡违。托精灵之运会兮,浮日月之余晖。假淳气之精微兮,幸备宴以自私。愿申爱于今夕兮,尚有访乎是非。”这基本上与司马相如以来遇佳人于闺闼而以礼自持情形相仿,只是阮籍所依赖的为清虚之思,他“历四方而纵怀兮,谁云顾乎或疑?超高跃而疾惊兮,至北极而放之!”在骋怀高蹈中达到玄鉴的境界,他说:“既不以万物累心兮,岂一女子之足思!”[168]这也就是他所谓“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的至境了。此赋体现了阮籍以思辨遗情而非礼义节情的生命方式,显然是对此前儒学文艺观的一大突破。
虽然在思想方法方面,阮籍较其父辈乃至两汉的先辈都高明许多,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恐怕也没有达到忘情遗世的地步。《大人先生传》运用问答体,将“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挚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的儒家典范作为批判的对象,将株守成规的礼法之士比作藏在破裤棉絮中的虱子,最终只是被焚灭的命运;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又“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因此建立这种体系之上的功业名荣也都成为自欺欺人的产物。而“大人”、“至人”或“真人”则是“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以及“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169]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完全超越了以儒家学说建立起来的世俗伦理、现实政治、个体价值等内容,达到了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有力的发展了庄老学说中突出个体自我对精神自由无限追求的内涵。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他在突破儒家思想樊篱的同时,也突破了儒学文艺观的限制,强调表达个体自我的自由意志的新鲜主题,发展以想像、夸张、思辨、清逸、含蓄为主的新的文风,与嵇康一起成为正始文坛双峰并峙的傲岸景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