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时间划分及四纪元构想
刘 震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对历史记载和纪年极其漠视的民族。但是他们创立了纷繁复杂、包容巨细的各级时间概念,还对天文历算作出卓绝的贡献。较之其他文明古国,这些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印度天文历算及星象学的发展可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期。上古时期可从公元前1700年到前五世纪,即吠陀(Veda)时期。在吠陀时代末期出现了六支(Sadanga)研学吠陀的辅助学科,即吠檀迦(Vedānga),或称“经”(Sūtra)。天文学(Jyotisa)作为一完整学科,也成其六支之一。中古时期可推至公元六世纪,即天文吠檀迦时期[111]。这两个时期内并无该学科的专著存世[112],只留有出自宗教和文学作品的相关表述。最后的近古时期则从公元后六世纪早期至十六世纪,有专门的科学著作流传下来。
从这些贯穿三四千年的天文历算记载中可以梳理出两条时间观的脉络:家常历法和宗教历法。双方泾渭分明地自成系统,却在实际应用中水乳交融。尤其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甚。前者只能标示当下的日常生活,并单纯地学术化,萎缩在历算著作里。后者则将触须伸展到印度人世界观的十方三世,几乎成为所有印度语言[113]和文字记录唯一的时间界标。这个多少可以解释印度对现实历史的态度的原因。
本文准备讨论的是一些古老的时间概念,它们从上古传至中古,有些词汇还继续在现代社会被使用着。而上古和中古正是家常历法作为单个系统失语,不得不借助与宗教作品和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立言的时期。我们可以从中更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如何反映和影响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历史观的。
这些时间概念涉及的基本上只是吠陀宗教及其传承——印度教。印土的另外两大极具影响的宗教,佛教和耆那教,因为算作吠陀宗教的两条较为疏远的旁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这里不作赘述。
一、印度的时间划分和常用时间概念
1.夜(rātrī)[114]与昼(ahan)
在古代印度认为夜先于昼出现,如《梨俱吠陀》(Rgveda,以下称Rv,Rv.10,129.)所述,光和热从黑暗和寒冷中诞生。所以夜常直接成为日、天(tithi)的代名词。《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以下称Av,Av.10,7,42.)中,“正如我们还将见到,为与太阳年一致,依据太古所计算的,人们将十二夜续入太阴年之尾。”夜与昼常常表述为两个半天 半天(Rv.6,9,1.);或者干脆以“日、天”的双数形式出现,ahanī,dyāvā。
半天(Rv.6,9,1.);或者干脆以“日、天”的双数形式出现,ahanī,dyāvā。
2.晨、午和晚
晨在吠陀中被称为“乌莎[115]的曙光”(usaso vyusti)、“破晓”(vastu)、“醒来之时”(prabudh)、“清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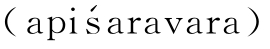 “在……东方乳牛的母亲(乌莎)扬起她的旗帜;她一再延伸自己,直到将父母(天和地)的怀抱充满。”(Rv.1,124,5.)[116]“在东方年轻女子垂下闪闪微曦,她给一列红牛套上挽具。现在她要发出光亮;她的旗帜则在先开道:火神阿耆尼(Agni)把自己装进那个房子里。”(Rv.1,124,11.)“如窃贼一般,那些星辰和夜晚的黑暗蹑手蹑脚地从此消失……”(Rv.1,50,2.)“即使是鸟儿也在你的光亮中从巢中高飞,人们【起身】进食。”(Rv.1,124,12.)“这是你的功绩,你高超的力量让无知者开窍,如果牲畜们集合在你周围,阿耆尼,只要你在早晨[117]被点燃。”(Rv.3,9,7.)
“在……东方乳牛的母亲(乌莎)扬起她的旗帜;她一再延伸自己,直到将父母(天和地)的怀抱充满。”(Rv.1,124,5.)[116]“在东方年轻女子垂下闪闪微曦,她给一列红牛套上挽具。现在她要发出光亮;她的旗帜则在先开道:火神阿耆尼(Agni)把自己装进那个房子里。”(Rv.1,124,11.)“如窃贼一般,那些星辰和夜晚的黑暗蹑手蹑脚地从此消失……”(Rv.1,50,2.)“即使是鸟儿也在你的光亮中从巢中高飞,人们【起身】进食。”(Rv.1,124,12.)“这是你的功绩,你高超的力量让无知者开窍,如果牲畜们集合在你周围,阿耆尼,只要你在早晨[117]被点燃。”(Rv.3,9,7.)
早晨放牛之前还得挤奶,所以晨又称为“挤奶时间”(sa Cgava);“突进”(prapitva)也是它的别名;此外,它还有“太阳神升起之时”(uditāsūryasya)、“此前”(prātar)、“此日前的”(prātarahnah)之名。
午的名称有:“日中”(madhya mahnām,Rv.7,41,4.)、“中”(madhye,Rv.8,27,20.)和复合词“中天”(madhya Cdina)。
晚和晨一样,名称可分为两类:一类依照神的名号和性格,另一类依照自然属性。萨维德里(Savitr,驱使太阳的神名,意为“驱者”)在早晨唤醒众生,晚上又让其恢复安宁。此时,整个自然响应萨维德里的指令,叫做“回归”(abhipitva),“突进”的反义词。Rv.2,38.生动地描绘了此一情景:“太阳的离开、出走”(uditi,nimruc sūryasaya)恰与“太阳神升起之时”对应;暮色开始隐藏自己,此时还叫做“暗”(dosā)。
以上都是雅利安先民最原始、最自然的时间划分,而且完全在一个自然天的内部。接下来,人为的成分渐多。
3.月(mās,māsa)
天的集合即为月。月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计。“……你(因陀罗,Indra)[118]把【他(毘梨多,Vrtra)[119]挂】在天上作为【一个】月的划分者;父亲(天)把这个被你劈开的当作圆盘挂起。”[120](Rv.10,138,6.)[121]
亘古不变的新月和满月的转换形成了这个民族家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中一段至关重要的篇章。新月之夜(amāvāsyā,amāvasī)和满月之夜(paurDamāsī)为半月与半月之间的结点(parvan)。新月之夜后的日子是白半月(pūrvapaksa,yava),此时月光增长;满月之夜之后就是黑半月(aparapaksa,ayava),月亮逐渐亏损。每月中分别祭祀四个不同的人格化的女神:新月日前一天的Sinīvālī、新月之日的Kuhū或叫Gungū、满月日前一天的Anumati和满月日的Rākā。
这样的半月,从新月夜至满月夜,或者相反,叫做“十五【天】”(pa1cadasˋa)。(歌者)“那些不信神者仗着自己的身板而趾高气扬,如果我真的和他们交战,那么我将在家里为你煮一头健壮的雄牛,还敬奉辛辣的苏摩(Soma)[122]十五天。”(Rv.10,27,2.)印度日耳曼宗教曾以自然为基础而建立,因此这些节日和自然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比如,“我们将带给你柴火,为你细心准备祭祀,在每个月相转换时[123]。让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那就是我们还能更长久地活着!——阿耆尼,因你的友情我们应不受伤害。”(Rv.1,94,4.)
这两个诗节提及的就是吠陀时代非常著名的新月和满月祭。在有关祭祀(yajur)的篇章中经常提到这两个节日。战神因陀罗是吠陀时期一位很重要的神祇,火神阿耆尼是祭祀的媒介——因为祭品(比如苏摩)要通过火送达所供奉之神。所以他们俩常是各类祭祀的主角,除了特殊需要,牛和苏摩是最常用的祭品,月相则是定位祭日的日历,祭祀的目的除了前面所引的求长寿平安,还有求财富(当时无疑是求六畜兴旺)。祭祀所表现的场面,或者说连同祭祀期内相关活动所表现的场面,常常是神的伟大功绩,特别是因陀罗的。在梨俱吠陀时期,这两个节日尚属草创[124],到了梵书(BrāhmaDa)时期,即吠陀时期的晚期,新月和满月祭的活动,每个家主须呈祭三十年[125]。
如果再将这一双半月拆分,那么可以得到星期。当然所谓“星期”在印度还是依照月相。在Av.15,16,2.提到满月之后的“八天”(astakā)。最重要的“八天”就是旧年的最后八天。在Av.3,10.里她[126]被称作年的夫人(patnī)和映象(pratimā)。日、天据她而轨范(泰帝利亚集Taittirīya-Sa Chita,以下作T.S.3,3,8,4.)。
一对半月的合并就成为月。月的时间跨度为一个新月到下个新月。太阴历一个月有29或30天。十二个这样的自然分割(354天)与太阳运行的一个周期大致相符;如果能由此调节得更为一致,那么就成了。
4.年(parivatsara,samvatsara)
如果按照太阴历,那么每年终了,相较于太阳历必然会有十几天多余。在三年里面将会累计到整整一个月。这个弊端早已被印度日耳曼民族所认识,并通过两个办法补救:要么将每年多余的十几天加入每年固定的时节之后;要么将累计下来的那个月作为某年的第十三个月。两种方法都曾出现在吠陀时代过。第一种方法更古老一些,出现于印度日耳曼史前时代。依此人们将十二天加入岁末,成为一个十二天的冬季二分点。这样354天的太阴年就可以和366天的太阳年一致了。
黎补(Rbhu)们是年的保护神,通过他们的转换使得其父母(天和地)焕发青春,他们十二天在无遮(Agohya)[127]的房子里休息。“黎补们十二天之久安睡着,在无遮的热情款待之下感到非常惬意——因为他们使得农田肥沃,使得河流改道。植被引入了荒漠,水流到了洼地。”(Rv.4,33,7.)“当你们,黎补们睡过头了的时候,你们问道:‘无遮!谁唤醒了我们?’公羊把狗叫做司晨。年关之后,今天你们把这个【世界】环顾一遍。”正如前面有关夜的概念中所引,这十二天常被称作“十二夜”。十二夜加入一年之尾,好比一年十二个月的映象(samvatsarasya pratimāvai dvādaŚa rātrayah,泰帝利耶梵书Taittirīya-BrāhmaDa,以下作T.Br.1,1,9,10.)。
以上说的是第一种太阳、太阴历的调整方法。第二种方法,亦即通过一个第十三月协调两套年历,同样见诸《梨俱吠陀》。“他(伐楼罗)[128]认得这十二个月和他们的后代,这个执法者;他认得那个后来出生的[129]。”(Rv.1,25,8.)
Rv.1,164.是一系列谜语,其中15颂为:“他们说,第七回(出世的)在那些孪生子中是单个的。(前)六是双生,被称作神生的仙人[130]们……”六对双生的即为天成的十二个月,第七回出世的便是后天所加的闰月。
徐梵澄所译之《五十奥义书》[131]中《考史多启奥义书》(Kausitaki-Upanisad,以下称Kaus.Up.)亦有描述月份和年的诗偈:
嗟尔诸季候!我自远光来;
聚集为精气,出于十五分,
祖灵之世界,以人为作者,
置我于母体;我生又重生,
为十有二分,或十三连月,
是由十二分,或十三分父。
我知此且知,与此相对者。
嗟尔诸季候!导我至永生!(Kaus.Up.1,2.)
正如很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在印度,年历里面加入闰月也是历法的一大进步。何时加入闰月也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太阳来回偏移的细心观察,或者,这样的猜测也不无道理,基于对星宿,尤其是五大行星运转的认识。根据太阴年和太阴月所计:十二个月,每个月有三十天,每天从太阳升起到再次升起(ahorātre)[132],形成了一年360家常(sāvana)日。五个如此的年(1 800天)构成一个周期,在该周期的末尾加入一个同样三十天的闰月。这样的算法就是一个五年的周期(pa1caka yuga),并恰好和一个木星运行周期相合[133]。
5.纪(yuga)
它在《梨俱吠陀》被提到:“现在我们愿向你们这些人宣布英雄的骏马车驾。诸神知道。在六行中,每行五个和五个地套上,从此出行——伟大的是唯一的神力。”(Rv.3,55,18.)六行,每行成双为十二,指的是一年十二个月;倍之以五,正好是一个周期;骏马加上马车上的英雄正好是60+1个月,一个完整的五年周期。套辕这个动词的词根是yuj,从此衍生出yuga这个名词。印度的一个计程单位,由旬(yojana)亦是从该词根派生出来,意指将牛套一次挽具,车所行的路程[134]。因此,yuga可理解成这样的一个比喻——“月车”套一次挽具在时间上的行程。
谜语系列中的Rv.1,164,14颂唱道:“配上轮辋,这个轮子永不磨损地转动着;十匹挽在辕上。太阳之目行之,即使笼罩在浓雾里。众生于上而立。”那十匹【牲畜】(dāsˋayuktāh)无疑是五年纪里的十个半年(ayana)[135]。在此组歌中还有:“这个十二条辐的时间【秩序】之轮永远绕行天空,因为它永不磨损。阿耆尼,720个儿子成对地立于此上。”(Rv.1,164,11.)十二还是十二个月,720是360对昼夜[136]。“十二块辐板[137],一个轮子,三块毂:谁能明白?其中有360个【辐】,如栓子一般,固定,它们不会松动。”(Rv.1,164,48.)这里是一年和其中的三个成对的季节[138]。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方便比喻,或者为了方便日常和宗教生活使用,吠陀时代时间的划分皆是整数。然而实际的天文观测结果并非如此理想化。就我们的一般常识而言,一个月应该是29天半左右,这里的天指家常历的天,即太阳两次升起之间的时间。而一个太阳年应该是365天半左右。因此一个真正的五年纪应该会多余两个月。在吠陀时代后期的梵书中,规定了一个五年纪中和末各加入一个月[139]。而在属于中古期的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以下称Mbh.)中,毗湿摩(Bhīsma)向难敌(Duryodhana)讲述,对般度五子规定的十三年流放期如是计:在每五年里加入两个月,因此共计加入五个月零十二夜。(Mbh.Ⅳ,52,第1606“颂”)。
虽然吠陀没有给出明确规范哪一部历法,而后期的梵书也没有依吠陀中所隐喻的那样的时间划分来导出一个360天的纪年,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印度先民没有认识到如后来那般精确的划分方法,吠陀的旨趣并不在阐述完全天文学的历法。Av.6,128,3.中的诗句可窥当时厘定历法所要关心的对象:
ahorātrābhyām naksatrebhyah sūryācandramasābhyām/
bhadrāham asmabhyam rājn chakadhūma tvam krdhi//
“为了昼与夜,为了星宿们,为了太阳月和太阴月,哦,国王,牛烟[140]!请你为我们创造好时节!”
即便是“纪”这个概念,也不是总和五年期联系在一起的。在《夜柔吠陀》(Yajurveda)中还有六年、四年、三年,甚至二年的“纪”[141]。
6.季(rtu)
这里得插入一个月与月关联的概念——季。前面所引的Rv.1,164,15.中有六对孪生子之喻。根据和祭祀有关的婆阇沙奈义集(Vājasaneyi-Sa Chita,以下称V.S.)这六对【季节】(每季两个月)为:春季(Vasanta,有Madhu和Mādhava两月)、夏季(Grīsma,有Śukra和Śuci两月)、雨季(Varsā,有Nabhas和Nabhasya两月)、秋季(Śarad,有Is和Urj两月)、冬季(Hemanta,有Sahas和Sahasya两月)和寒季(Śisˋira,有Tapas和Tapasya两月)[142]。
季的概念与天文观测无关,而是和气候有关。最简单的分季是冬(hima)夏(Samā),即冷热两季。在这样的季份周期中不依年计时,而是依冬夏[143]。另外,和以夜代天一样,印度日耳曼民族也常常以冬代年[144]。
春秋,作为连接冬夏的桥梁,在吠陀时代还没有取得和前者一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雅利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视农业生产的时候,第三个季节被添加进来,那就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秋天。因为农业的地位逐渐提高,所以在吠陀中,当人们许愿长寿时,比起说“愿活上一百个冬天”,更偏向于说“愿活上一百个秋天”[145]。春天是最后加入年季的。该词在《梨俱吠陀》中只出现了两次,而且都是在第十书里[146]。
由此也可见,吠陀时代季的划分主要是三分法(六也是三的倍数),即:春天和初夏,仲夏和雨季,秋和寒季。今旁遮普邦正是雅利安人入印的第一站,根据天气所定的三季至今仍在当地运用。在印度斯坦(印度河流域)直到现今每四个月,即每季开始之时,还有节庆(cāturmāsya)。在古代则是祭祀日。
当雅利安人从旁遮普向东南进军后,所面临的气候也随之变化,所以五季替代了三季,即六季中最末的寒季并入春季。当然六季也并存着。此外,还有种分法,就是七个季节。那第七个就是闰月。第七季没有固定的名称,因为它不是基于气候产生的,只是个人为的创造物。
7.吠陀的宗教仪式历
如前所述,此时的印度历法宗教色彩浓重,它不仅将所有计时方式神话化,而且为宗教活动——祭祀本身服务。
奥博里斯(Oberlies)在他的《梨俱吠陀宗教》一书的第二册《苏摩和梨俱吠陀宗教》中1.6.5节“吠陀的宗教仪式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精彩总结。正好也可作为本文在此的一个小结[147]。
“各类仪式在固定的时间举行。吠陀的‘宗教历’[148]——亦即‘宗教体系的具体可行的规范化形式’——根本上定位于一天和一月之始,于岁末,并且依此【定位】一般地遵循吠陀氏族社会的生活节奏。如同在其他社会中于时节交替之际——如,太阳和年的更替,月和季的转换——举行宗教仪式。如此在进入下一个季节之时,则举行四月(cāturmāsya)大会,正是将一年所分为各个季节的反映[149]。同样两个月/半月之间的‘接缝’标志着新月和满月祭的时点。新月和满月祭可能在梨俱吠陀时已有,保守一些的话,阿闼婆吠陀时肯定出现了。此外,每天在昼夜交替之际会举行一个小仪式。而新旧年的更始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点,那时会有一个隆重的新年节庆。”
其他的仪式还会在这些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时点上举行:如征伐的开始和结束,以及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这些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段落。“即使是这些仪式也或多或少地镶嵌进一年的历程中:征伐,作为一个‘季节的活动’——其抢夺对象主要是牛和粮食——通常在收获时节,即初夏和深秋进行,而成年式(可能每次为同庚者举行)则在雨季开始时举行。”[150]
8.其他时间单位
至此,划分时间的最小单位不过是三分之一天。在吠陀时代后期,又发明了较之更精细的各级时间单位,并将所有单位系统化。
在《百道梵书》(Śatapatha-Brāhmana,以下简称Ś.Br.)12,3,2,1中,从年开始,依此类推各级时间单位,在“一年为……720昼与夜”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间单位——牟呼栗多(muhūrta),“【一年为】10800牟呼栗多”。该词原先在《梨俱吠陀》中只有“瞬间”的意思[151]。而在梵书时期除了原意外,还具体到1/30天或者48分钟。接下来,“每个牟呼栗多有十五etarhi(原意为[152]:现在);每个etarhi有十五个idāni(现在);每个idāni有十五个prāDa(呼吸)……”后面的单位皆是前者的1/15,ana(呼吸)、nimesa(眨眼)、lomagarta(毛孔)、svedāyatana(汗腺)等等。
在《摩奴法典》(Manu之Dharmasˋāstra,以下称Mn.)[153]1,64中有另外的划分体系:“十八瞬间(nimesa)构成一迦什陀(kāsthā);三十迦什陀构成一迦罗(kalā);三十迦罗构成一牟睺多(muhūrta),同样数目的牟睺多构成一昼夜。”
类似但不尽相同的时间单位罗列见诸各类往世书(PurāDa)和《政事论》(Arthasˋāstra)[154]。
玄奘法师也通过他所译的《阿毘达磨俱舍论》和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向中国介绍了印度的历法和时间划分。“时极短者。谓刹那也。百二十刹那(ksaDa)为一呾刹那(tatksaDa)。六十呾刹那为一腊缚(lava)。三十腊缚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为一时。六时合成一日一夜。”[155]而后还有对日、月、年、季的介绍。此时季分六或四,每月的起讫分明,并且按星座定名。该篇在季羡林的《西域记》校注本中名为“印度总述岁时”,其所记述没有专于佛教,可看作中古时期印度家常历法的一个概览[156]。
那么宗教历法在此时有何发展呢?
其最重大的发展无疑是四纪元的构想。“纪”这个单位大到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使用它,所以它可以脱离家常历法在宗教传说中天马行空地发展。
二、四纪元的来历
《摩奴法典》中说道:“现在你们可以扼要和循序渐进地学习何者为梵的一昼夜,以及何者为四时代中每一时代。”(Mn.1,68.)
“四时代”,本文称作“四纪元”(caturyuga)指的是由四个漫长的纪组成的一个时间组合。这四纪分别为:圆满纪(k rtayuga)、三分纪(tretāyuga)、二分纪(dvāparayuga)、末世纪(kaliyuga)。“一切称柯利多、多利多、陀跋钵罗和伽里[157]的时代,系于国王的行动。”(Mn.9,301.)
纪(yuga)在吠陀时代主要还是表示一个数年的周期。通过这个周期可以协调不同的历法体系。它也偶尔被用来指代一个非常长的周期。比如Rv.10,72,2中“devānām pūrvye yuge”指的是“在诸神的久远的时代”。在Av.8,2,21中一个纪被列序在一百年、一个阿由他(ayuta)[158]之后,然后再是两个、三个、四个纪。在T.Br.3,12,9,2中它被认为有十万年长。
在《阿闼婆吠陀》的陈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当时存在着这样的说法,即纪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的组合。
在《梨俱吠陀》中出现了“triyuga”一词,“这些在诸神之前诞生的药草,比那triyuga都早。”(Rv.10,97,1.)据难近母陀娑(Durgadāsa)所注《话训》(Nirukta),该词被诠释为“三纪”,即以药草的视点,那“三纪”指的是四纪里的后四纪,它则诞生在第一纪;或以我们人类的视点,药草诞生于前三纪之前,我们生活在第四纪。这样的诠释明显带有中古期文学和宗教的烙印。而Sˋ.Br.3,2,4,26中的解释则为“三季”,即四季中的前三季。“triyuga”是否为一个三时段的组合体,还是四纪元的一部分,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纪元组合为何为四?它们的名称来历又是什么?
迄今为止,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是骰点说,另一类为月相说。
很多印度学大家,诸如韦伯(Weber)、罗特(Roth)和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等,皆持第一种观点,而这一观点也为大众所认同。
掷骰是流行于印度的一种古老的赌博游戏,Rv.10,34.就有对赌徒生活的形象描述[159]。最早提到前述四纪同名的词汇的是V.S.30,18.和T.Br.4,3,3,1;2。但是它们所指是单纯的骰点还是隐喻性的四个时段,则模棱两可。甚至有说,与其是将某四个时段比作骰点,毋宁说是前者为后者的喻体[160]。在一个对《唱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ad)的注释中有这么一句:“当余下四点就是krta,三点就是tretā,两点是dvāpara,一点名叫kali,当krta通过饬令被召唤时,为胜利的一掷这些骰子将征服下面的(骰点),点数小的将屈从于大的。”[161]这里可以知道四个名称的优劣顺序。在爱多列雅梵书(Aitareya-BrāhmaDa)中提到,“kalihŚayāno bhavati samjihānas tu dvāparah,uttisthans tretābhavati krtam sampadyate caran.”译文为:“躺着的是kali,起身的是dvāpara,站立的是tretā,行走的是krta。”[162]虽然这里还是含义不明,但是在Mn.9,302紧接着四纪的条例(9,301)同样是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摩奴法典》中已经被用作对四纪,而不是骰点的评价了。到了中古时代,在史诗和往世书中,这些有关掷骰的章句一再被引用,意义自然只有一个——对四纪元的描述。从四到一的点数正好表示每纪人类福德的数量:“在第一时代,正义藉牡牛之形,四足稳立;真理流行,人有所获,无一来自不义。在其他时代,由于财富和知识非法取得,正义相继失其一足;而由盗窃、虚伪、诡谲所代替的正当利益逐渐减去四分之一。在第一个时代,人免于疾病,得遂享寿四百年;在第二及其以下时代,生命渐次失去其存在时间的四分之一。”(Mn.1,81-83.)
另外一种起源,即月相说,只由韦伯一人主张。四纪还有一套名称为:圆满纪(krtayuga)、竭栗婆纪(khārvāyuga)、二分纪(dvāparayuga)、弗沙纪(pusyayuga)。他的观点基于二十六梵书(Sadvi CŚabrāhmaDa),“在pusya由第二个四分之一主宰,在dvāpara第一个四分之一,在khārvā是满月,在k rta是新月。”骰点之说他也赞同,不过他仍认为,骰点起初是表示四个月相,然后再衍生到四纪元的。这个假设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以月盈为善、月亏为恶,那么善恶在月相中是交替出现,而不是由善到恶递减的。韦伯坚持认为,月相的四分是人类认识的第一个四分法,所以自然而然地运用到四纪元构想中去了[163]。
综上所述,四月相、四骰点、四个时间段,孰先孰后都无法定夺,何况这两派观点的对错优劣?在此笔者斗胆补充一点,四纪元构想成形期,四季的划分已经在印土流行。如果把春季视为最积极的,冬季则为最消极的,如果把四季对四纪元的影响考虑进去,不仅可以让四纪中的衰减理论找到一个时间上的缩影,而且可以向中古时期四纪元循环往复的理论提供现实依据,即每次从末世直接到圆满纪,好比从冬到春。另外,“triyuga”一词同时亦可以有“三季”、“三纪”两种解释。
那么每纪以及四纪元到底有多长?
《摩奴法典》说道:“据贤者称第一个时代是由四千神年构成的。先于它的黎明是由同数的百年构成的;后于它的黄昏亦然。”
“在前后同样都有黎明黄昏的其他三个时代中,十年和百年内依次递减一个单位数。”
“上述四时代总计,为数一万二千年,称为诸神时代。”(Mn.1,69-71.)
“上述包括一万二千神年的诸神时代,重复七十一次,这时叫做摩奴时期(Manvantara)。”[164]
“摩奴诸周期和世界的创造与毁灭一样是不计其数的,至高无上的神使它周而复始,有如游戏。”(Mn.1,79-80.)
原先四个纪元只是从四千人年依次递减,而后,每纪的始末插入一个黎明和黄昏时代作为过渡,最后,神年替代了人年。一个神年等于360个人年[165]。那么一个完整的四纪元周期就相当于4320000人类的年。
原先类似于希腊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四纪,印度的四纪元也是单向不循环的。但是后来在往世书时期又有了更大的时间单位——大纪元和劫;四个纪元组成一个“大纪元”(mahāyuga)或者叫做“四纪元”(caturyuga),千个大纪元构成一劫(kalpa),一劫结束,再来新劫,劫也像纪一样有多类,再组成一个周期,大周期套着小周期。这样时间就以四纪元作为一个基本节拍单位循环不止了。
三、四纪元的描述
所有文献对四纪元的描述,其共性就是由盛至衰的递减。
《蒙查羯奥义书》(MuDdaka-Upanisad,1,2,1.)言道:“智者所尝见,诗颂中法仪,乃在三一世[166],多方覃敷遗。”
《摩奴法典》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章句还有:
“吠陀经中所宣示的人生,行为的果报,生物的权力,都结出与时代相应的果实。”
“随着这些时代的递降,某些美德为第一时代所特有,某些为第二时代所特有,其他一些为第三时代所特有,其他一些为第四时代所特有。”
“在第一时代,以苦行为主;在第二时代,以神学为主;在第三时代,以完成祭祀为主;在第四时代,据贤者说,只以乐善好施为主。”(Mn.1,84-86.)
在《摩诃婆罗多》第三书中有两处描写四个纪元,一简一繁,均由智者摩根德耶(MārkaDdeya)向般度五子(pāDdava)之首,史诗主人公之一——坚战(Yudhisthira)授记。先列出简述的部分[167]:
“圆满(krta)【纪】,我亲爱的[168],即是一个正法未断的时代:于彼良时,【一切】已作(krta),无应作。法规有效,生灵不朽;因之此序列中视圆满纪为最。神、恶魔、健达缚、夜叉、罗刹和蛇类不存,我亲爱的,买卖也不存。人不知娑摩、梨俱、夜柔【吠陀】之所书,《摩奴法典》亦不知:唯修正法和苦行为功。彼时无病患、知觉无衰;无怨,无悲、无骄、无厌;无诤、无疲、无仇恨、无畏、无痛、无忌妒。是以无上之梵为智者最高目标,众生之灵——那罗衍(NārāyaDa,即毗湿奴Visnu)为白色。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虽因本性而不同,但在圆满纪共同生活、各尽其职。人唯有一个职责、一种风纪、一个想法;因为彼时诸种姓通过同一种作为履行义务。永远皈依唯一之神,通过对他的崇拜和不同方式的供奉,并且以一部吠陀、一个戒律为规范,通过遵守四个生命时期(āŚrama)[169]不同的【婆罗门】纪律——这些纪律都是对治欲望的境相——来达到最高的目标。
“此正法——建立在所有心灵的认识之上、并由此形式各异——在圆满纪有四部分,并为四种姓共同适用。此圆满纪远离三德。”[170]
“现在请听三分(tretā)【纪】!在此纪出现祭祀活动,正法衰减四分之一,那不朽者(毗湿奴)变成红色;那些精进于神职和正法的人们具有喜德(sattva)。在三分纪里,现在祭祀、风纪和各种应用——情和愿——大行其道,以求圣业和布施之果。行忏悔和布施使其不远离正法;三分纪的人履行义务,精进于善业。”
“在二分纪正法只得二分之一;毗湿奴为黄色,吠陀一分为四。某甲得四部吠陀,某乙三部,复某丙二部,某丁一部或全无一圣歌。若典籍如此分裂,主持圣仪亦各式各样。人们行忏悔和布施具有忧德(rajas)。因不识唯一之吠陀,则将一分为多;本质已失,只存【相对】真理。彼从本质(善的准则)而堕落者将会受疾病侵扰;受欲望和厄运所困,因此人们为热恼所迫。另有人等,进行祭祀,为求愿望满足,抑或天之资财。如是因正法缺乏,在二分纪众生堕落。”
“在末世纪,哦,贡蒂之子[171],正法仅存四分之一;在此暗德之纪,卷发者(毗湿奴)为黑色(krsDa)。吠陀的秩序停止了,正法和祭祀仪规亦如此。瘟疫、疾病、疲惫、嗔怒和其他过患、灾禳、惶恐、饥饿和怖畏迷漫于世。如若世纪的轮回再次重复,正法也将再回转,并且随着正法回归,人类世界亦再出现。动持之情感会随人世停止;随纪元没落而立的风纪,人之所愿亦会改变。”
以《摩诃婆罗多》为首的史诗和《往世书》是印度教从吠陀宗教脱胎,成为今天我们所见面目的两大文学源泉。前者成书于公元前后五世纪间,即于笈多王朝(公元320—500左右)中叶完成结集。被印度教称“第五吠陀”。后者,作为一系列《往世书》的集合,成于公元前不久到公元一千年。两者之间有五百年时间交错,所以很难说清在某些内容上是何者出自何者。
“印度传统把《摩诃婆罗多》当作‘历史传说’,和另一些书籍归为一类。这些书籍的总名是‘往世书’,意思也就是‘历史传说’。”[172]在和吠陀时期宗教和家常历法没有明显界限的情况不同,在此中古时期,理论上存在过的专门历算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宗教性的文学作品被当作正史,那么历法纪元也只能从中读取了。更有意思的是,近现代的印度教徒一旦援引吠陀,那一定不是指真正的四部吠陀,而是指史诗和《往世书》里对吠陀的想象,甚至就是这两者的内容本身。
中古期的宗教由吠陀时代的多神崇拜变为一神信仰。印度教里最大的一支便是崇拜毗湿奴的。通过史诗和大多数《往世书》毗湿奴的唯一主神地位终被确立。所以这些书通篇充满毗湿奴的言教和信徒的崇拜。
《摩诃婆罗多》第三书中第二次的四个纪元的授记远比第一次冗长,另外的第一、六、十二书还有相对零散的描述,它们在不少地方和几本《往世书》——诸如《诃利世家》(Hariva Cśa)、《薄伽梵往世书》(Bhāgavata-PurāDa)、《毗湿奴往世书》(Visnu-PurāDa)、《伐由往世书》(Vāyu-PurāDa)、《摩根德耶往世书》(MārkaDdeya-PurāDa)、《梵转往世书》(Brahmavaivarta-PurāDa)等——共成互文。在此仅作一个概览,与前文重复之处亦从略。
在圆满纪,祭司通晓吠陀,苦行者功德圆满。人们供奉那罗衍并颂神咒。国王有权保护下臣并只收取1/16的税收[173];婆罗门免税赋并且到处受尊敬。学生服从老师,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只有适孕期夫妻才可同房,并且不是出于肉欲,丈夫不在外通奸。那时人们健壮、高大并且俊美。他们得享长久的青春和千年的寿命。所有人心灵纯净,没有恶人。举世回响着高贵者的赞歌、名人格言和祝词。每家每户在月的结点[174]祭祖,月历的规定几天祭神,客人天天受敬;下等种姓服从和供养婆罗门。没有亵渎神灵、婆罗门和隐修者的人,也没有那些自我神化的人;所有人都为他人的优点而高兴,并为他人谋福利。自然界也和人世间相应:大地上作物丰收,满布宝石。
还有的描述神话色彩更浓重些:大梵天为每个种姓创造一千对男女;那时女人没有月经,所以夫妻只有通过念头来产生下一代。那时也没有季节变换,气候不冷不热;大地上没有植物,没有禽类和牲畜,但会冒出一种汁液充当食物。人们住在山间水畔,没有定所;人们无所欲,无憎恨,也无天敌。人之所需随念即生,从这些物体产生出汁液,使得人们具有神力,扫除一切衰老。人们形象和寿命皆相同。人类的身口意都没有善恶、甚至没有施者和受者的差别,也没有种姓差别。
在圆满纪的末后,时间【之神】(Kāla),毗湿奴的一部分,带来了罪恶,唤醒了情欲和争讼,而它们从无明和贪中产生。人类与生俱来的八种神力消失了;人们感受到了冷热,幸福一去不返。因为人类充满了忌妒和私心,欲将原先能生食物和衣服的如意树用藩篱据为己有,如意树(Kalpa-Vrksa)也消失了。女人在生命行将结束时会来月经并生儿育女;人类遭受死亡之苦。为防护突如其来的雷击,人们在山上和树上建屋并围以四壁和围墙。因为饥馑而产生了手工业和农业。为躲避互相之间的追逐,人们藏入无法进入的山区,住在峡谷和荒野里。
在这些具体的描述中可以找到很多原始社会的痕迹,特别是圆满纪末期的世风堕落,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萌芽期很相似。
随后的第二、三纪的描述就显得千篇一律、单调平白了。(https://www.daowen.com)
描写最丰富、最生动的无疑是最后一纪。末世纪——kaliyuga中的kali,它的含义除了前述之最小的骰点,还可能源出kāla一词[175]。该词有两个意思:一为“黑色”——恶魔的颜色,一为“时间”——毗湿奴所遣之造罪神,即时间的人格化神。此外,有一词根√kal,有“驱赶、逼迫”之意[176]。正可以对应《摩诃婆罗多》十二书,第361“颂”:
rāj1ahpramādadosena dasyubhihparimusyatām/
asŚaraDyahprajānāmy ahsa rājākalir ucyate//
“由于国王骄逸之过,【国土】将被达休[177]劫掠;
不做其子民救护者,彼国王被称作‘歌利’(Kali)。”[178]
末世纪的特征即如Mbh,Ⅲ180,v.12838所说:
viparītaŚca loko’yam bhavisyaty adharottarah/
“彼世界被颠倒过来,最低下的成最高的。”
首先被颠倒的是季节,雨水不再按时降落,作物不再丰收。饥饿的人们沿河种植蔬菜,但收获不丰。最常见的树木是Śamī树,人们从中只能收获稗草子[179];牛草[180]也是最好的【充饥的】草……人衣AŚvattha树皮,大地要么荒无一树,要么树木不结果实。边远地区渺无人烟,城市里盘踞着野兽猛禽,哪怕在塔里。同时,牛濒临灭绝;因此人只能饮羊乳。一岁的牛犊就得套轭,在沼泽里耕地……人们衣食住匮乏,所以身子无力而矮小,受各种疾病折磨。他们的寿命也很短,很多很早就夭折了。少女五到七岁就有孩子,少年八到十岁就为人父;十二岁头发灰白,没有人能活过二十岁;因为病、饥、渴,人们大批地死去。人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居心叵测;因为他们舍离了吠陀的道路、信服了无神论者,所以不能尽享天年。
肢体的退化应归因于精神和风纪的堕落。最重要的就是种姓制度的倾圮,它所树立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的权威也被颠覆。圣典吠陀也不再作为行为的准绳。祭祀、布施和戒律不再被实行,或者只是作为谋取自利所用和作为表面幌子。每句随心所欲的话语都可作为圣言,随意每样东西都可作为神祇,所有生活方式都是修行。首陀罗可以和婆罗门一样使用神咒。许多人以教授吠陀图钱,圣地也以赢利为目的。即便是婆罗门也讥讽吠陀,用世俗的歌曲赞美神祇,使用粗语并行邪淫。人们不敬祭火、神祇和客人,不给亡灵以水供。人们不信后世。很多人是因缘论的信徒,只凭现量和比量来量知【所缘之对境】[181],譬如数论师(SāCkhya),或者独自量知,譬如顺世论师,并且轻贱吠陀的启示。大多数人为无神论者,毁弃戒律,追逐世间法。首陀罗们长着白牙,涂抹眼膏,剔除须发,披上黄袍而习法,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生活。佛教的塔代替了婆罗门教的圣迹;大地充满这些人,当神庙消失,神祇毁弃之时。除此之外,还有露形外道(Nirgrantha)、髑鬘徒(Kāpālin)、左手师(Vāma)、兽主徒(PāŚupata)、五昼夜徒(Pā1carātra)等外道。世界充满外道,他们以各种服饰出世,并且擅自印证见地。隐修林被外道所占,作为款待宾客之所。乳牛将不再作为圣畜被礼敬,而只是因为产乳而畜;大地只是因为她怀抱中的宝藏而被赞颂,但不再作为女神。华服亦为俳优所着,任何一个水域皆可作圣地。人们可以花很少的气力得到功德和戒律的圆满……
法的倾圮表现在生命阶段(āŚrama)[182]的漠视和种姓及其义务的混淆。青年们无需受戒即可入梵学;家主不祭祀不布施;林修者贪享施食,乞食者结集亲友。梵行者因贪财而游荡、酗酒还和师母有染。婆罗门不再佩标识,贪图美食,和下等种姓交往。首陀罗对婆罗门粗暴无礼,后者反而称其为“圣”(rya)并恭敬他们。谁还说圣语,被视为空谈。种姓混杂,人们对一个被驱逐出本种姓的人不觉羞耻。刹帝利和吠舍也无视自己的义务;国王——现在多数是野蛮人或首陀罗——不保护其臣下,反通过高税收来压榨他们。由婆罗门引导他们巡游国土,讨取布施。国土荆棘满布。他们充满贪婪和无明,表面打着正义的旗号。他们抢夺下臣的财物,奸淫其妻,无视其号呼;还让人杀死女人、儿童和乳牛。在他们的统治下种族灭绝。贵族身份由财产决定;谁有马匹、车辆和大象,谁就为王;在末世纪有很多贵族。但是刚一上台就被颠覆,特别是一个为正法而努力的国王,不能活得长久。人们不识法制,不给他人庇护,反伤害他人。个个相逼,人人自危。戒律的约束已经断裂,凡事肆意决定,不用听他人劝告。人生的意义只有财货;一个向另一个乞讨、欺骗、掠夺……一个窃取另一个。在争讼中谎言造就了正法。每个都是无所不知的人,每个都觉得自己是智者。商品只有靠吹嘘才能卖掉,商人采用一切诡计。担保物将不再归还,因为人们宣称从未收到过。欺骗和忌妒毫无收敛,人们犯错毫无愧疚。只有不公正的报酬才会丰厚,正义者短寿和贫穷。到处是乞丐,但是没有施主。人们拿取施舍毫不迟疑,即使是一个低种姓的给的。如果主人贫困了,仆人就抛弃他,好像自己是最高贵的;而主人也折磨那些不幸的仆人。
夫妻之间的纽带也崩裂了,婚姻的缔结不再按梵仪和种姓法度。一个来自任何家族的有权势的人,可以娶任何种姓的姑娘;同时强奸也可视为结婚。没有求亲,也没有问聘,只有女子自己择婿(svaya Cvara)。男女的行为完全自由,互相无需忍让。性欲将夫妇结合到一起。妻子不服从丈夫。如果丈夫或公婆命令她,她会抓挠头发,并且撂摊子。她们没有戒律和教养,没有约束和理智,放荡、饕餮。她们有很多孩子,但整天杀死爱的果实。在所有家庭里,她们都是慕男狂;她们欲壑难填,而行邪淫,和奴仆、牲畜交合。即使是英雄的妻子也偷汉子。没有一个寡妇让自己和夫君一起火焚。在家里女人做主。那时男寡女众,而且男子惧内。
末世纪的尾声,世上的苦难达到顶峰。残暴、贪婪、灭绝人性的国王们和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迫使人们向那些无人区,向着印度河岸,向着月分河(Candrabhāgā,今Chenab河),向着迦湿弥尔,向着野蛮人居住的边地,鸯伽(Anga)、孟加拉(Vanga)、伽陵伽(Kalinga)、弥迦罗(Mekala),向着王仙河(Rsīkā)畔的群山逃遁。他们住在喜马拉雅的山坡上,盐海的岸边,野蛮人部落的森林里。
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的毁灭(pralaya)。一个普通大纪元的末世纪的结束,和一个劫的最后一个大纪元的末世纪终结,描写上都差不多。在末世的最后干旱将会持续很多年[183]。地平线上腾起烈焰,星光失色;星象显示出不祥,彗星横扫天际。太阳在升起和落下的地方被密云遮蔽,或者被罗喉(Rāhu)吞噬,也即日食。然后天上出现七个(或十二个)太阳,晒干所有的水系,将一切草木化为灰烬。接着飓风吹起破坏之火(Sa Cvartaka),为太阳烤干的大地裂开崩入深渊(Pātāla),令神魔惊吓。在一劫的终了,毗湿奴化身为暴恶神(Rudra),吞噬一切生灵;他是摧毁世界的“时间之火”(Kālāgnirudra)。他会化作世界之蛇——“余”(Śesa)的灼热的呼吸,将地狱、大地、空界(Bhuvarloka)和天界(Svarloka)吹作灰烬。三界[184]一片火海,好像一个油锅。最后巨大的云团,好像象群,并装饰着花环般的闪电,布满天空,闪烁着五颜六色。雷鸣中五彩的雨水淹没了整个大地并熄灭了破坏之火。暴雨持续十二年;世界之海高过海岸,在洪水中山崩地陷。当洪水触及七仙人星(大熊星)的区域,将停止高涨;毗湿奴的呼吸将化作劲风,吹了一百年,直到密云飞散。这样,风也被吸回,毗湿奴再次趟在“余”的身上,沉入瑜伽睡眠。
这样也是一个梵天的日夜结束。相对于昼至夜逐步趋近,夜至昼就转瞬即来。从圆满纪到末世纪要经过四个纪的递减,而最下劣的末世纪结束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下个大纪元的最美好的圆满纪。四纪元的更替是对昼夜交换模式的模仿[185]。
重新恢复这美好时代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完全自动的(svabhāvāt)。就像草在热季自燃,而后自动萌发一样。如此周而复始在一个摩奴时期不会中断。另一种则出于道德因素。当人类的苦难达到顶峰时,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罪愆,并厌倦了尘世。他们重拾正法,重新苦修,使得世界再次回到圆满纪。
至于原先描写过的物种灭绝中,人类何以保留繁衍的种子,在所有的讲述中都没有提到。之前还有不少前后矛盾的漏洞,使得整个四纪元的描述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但是这毕竟不是纯粹的“历史传说”,其布道功能永远是第一位的。
但这些文学作品也隐藏了“历史传说”的痕迹,看看印度公元前五世纪以后一千年内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些痕迹。
中古时期的印度经常被外族侵略。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就到过印度东北部,他身后留下的一系列希腊化国家也时常占领印度的一些地方,公元前一世纪又由塞种人代之;而后月氏的贵霜王朝统治了整个印度的上半部,在公元四至五世纪间白匈奴入侵。所以史诗和《往世书》中屡见外族军队和国王也不足为奇了。
前文还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或者学说被提到,这个在其他宗教文献里也可以得到佐证,比如佛教经典里对各种佛教徒眼中的外道的描述,还有大藏经中以批判为目的而翻译的《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等。对印度教来说最大的两个外道就是佛教和耆那教——前文之露形外道就是其一分支,而最具威胁的还是佛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着笔墨最多。佛教主张平等,其圣典人人可教学,就是对印度教的根基——种姓制度的最大冲击。虽然印度历史上两大圣王: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诸教并奉,但从现存文献来看,似乎最尊佛教。公元一世纪为佛教最鼎盛时期,印度教为其所压制,所以在前文中流露出深切的恐慌。
“历史传说”里末世纪的道德沦丧也并非子虚乌有。
君臣关系确实面临危机。中古时期的朝代更替频繁,其形式除了外族入侵,不外乎下臣僭越王位,孔雀王朝(公元前320—公元180或185)的奠基人,阿育王的祖父月护(Candragupta)也是如此。
当时的社会道德风貌还在世俗文学作品里有直接反映,即以《五卷书》、《故事海》为代表的故事集和以迦梨陀娑、檀丁为代表的经典梵语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者作者的年代都无法确定,但是定位于中古期还是没有异议的。除了有故事讲述类似的君臣关系,也有讲述夫妻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妻子贪淫无耻,还会谋害丈夫。主仆关系亦是如此,妻子常常和仆人勾搭成奸。
女子自主选婿可以在《摩诃婆罗多》中的两个插话《那罗和达摩扬蒂》、《莎维德丽》找到原型。
四个种姓也不能履行各自的道德义务。故事中,婆罗门常常以穷酸可笑的形象出现。在檀丁的《十王子传》中,为夺取王位和女人不择手段,不仅是社会上的家常便饭,而且还会受到称颂。即使是在被印度教奉为圣典的两大史诗里,英雄般度五子和罗摩都使用过不光彩的手段战胜对手,却还能被判定为符合正法。佛教典籍中商人的崇高地位,佛教和耆那教中首陀罗甚至种姓外的贱民修成正果,在印度教眼中都是非法。
还有很多民间故事,渐渐收入宗教圣典,但还是保留了描摹当时社会风情的生动笔触。比如佛教的本生故事。
虽然印度人似乎极力避免直接记录历史,但还是流露了现实生活在他们心灵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末世纪是现实的写照,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不过,我们的现实处于印度“历史传说”时间上的什么位置呢?冯格拉森纳普(v.Glasenapp)和雅柯比(Jacobi)根据《毗湿奴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推算,我们处在某个大纪元中末世纪的黎明。而该黎明期始于公元前3102年[186]。如果再套以劫,那么我们的历史在其中真的是沧海一粟了。难怪抱这种时间观点的印度人漠视历史记载和纪年,将历史看作简单的循环往复,并且为了适应这一说教模式,将史实同样抽象化,并打碎真实时间框架前后移植套用:就像这些中古期的史实在史诗和《往世书》里被置于我们所处的时点之后;还有说,能抵御外族、相对政通人和的笈多王朝为圆满纪的原型[187]。
至此我们或许会觉得,印度对美好的圆满纪的描述,类似于儒家对尧舜时代的幽思,完美但模式化;而末世纪描述,则与孔孟眼中的现实社会无异,丑恶但丰富生动。
四、其 他
印度对时间的四纪元构想还能在空间上找到对称点。印度的宇宙观把世界在地理上分成天界、中界和下界三部分。中界在中古时期又被印度教[188]设想为赡步洲(Jambūdvīpa)为最内的七个同心环形的大洲、每两洲间以七大海的形式。赡步洲七块以妙高山(Meru)为中心的带状地域组成,其中最南面的那块叫做婆罗多(Bhārata)。除了婆罗多之外,所有空间永远只有一种纪元:在下界自然是末世纪;在另外两界,只有和天界的一样的圆满纪,其人民的生活和神仙一样快乐,所以又叫做“受用土”(Bhogabhūmi)。婆罗多的人民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他们会反反复复地经历一个又一个四纪元。因唯有该地人民所作即于本地变现业报(karman),所以婆罗多又称“作业土”(Karmabhūmi)。也唯有此土之人民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得到解脱,出离轮回,所以此土最盛。
至此,谈了印度的时间概念,却没有提“时间”这个词本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的出现,相对于第一章里的那些关于时间划分的定义来说,要晚很多。“kāla”是最早用来表示时间的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在《梨俱吠陀》里,在第十书:
uta prahām atidīvyā jayāti krtam yac chvaghnīvicinoti kāle/
“并且,他超越对手的优势,将会获胜,当轮到他出手掷出k rta[189]时。”[190](Rv.10,42,9.)
对kāla一词,瓦克纳戈尔(Wackernagel)作了一番词源学分析[191]。认为古时的“r”后来可由“l”代之。kāla和kāra可以等价。后者出于词根√kr(“作,做”),意思是“使得如愿以偿的(机会)”,在骰子游戏里引申“带来最高骰点的(机会)”。后来在《唱赞奥义书》又有“kālam gacchati”的搭配,意思是“达到目的”。游戏里的用法逐渐隐没,而变为较泛泛的“决定性的时刻”,“吉时”。随后又取代rtu,表示“季节”、“月经期”。最后才形成广义的“时间”、“时点”。
不过,晚近的文学作品里,这个词在某些时候,还会体现它词根的意思。比如,“kālam√kr”这个搭配就是表示“死”,因为内有“做完、了结”的含义。这个也可以解释,在前文所提,毗湿奴毁灭世界时派出的神、吐出的火名字都叫“时间”(kāla)。
在史诗作品和佛教文学中,还有一词,从中引出,kālya,一样指“时间”。
另外还得提一个词,samaya。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是我闻。一时……”的“时”。这是个由表示“同,一起”的前缀sam-,和表示“走,来”的词根√i组合成的词。好像本意是一个数缘交汇的时点。
《印度格言》中有一句同时出现了kāla和samaya,这里抄录一下,可以玩味玩味它们的区别。
samaye suhrdahsarve sukhasampattilipsayā/
vipatkāle ca suhrdah svāngānyapi canātmanah//[192]
“在彼时(samaya)所有的朋友,希望享乐快点临头;
倒霉时候(kāla)莫说朋友,连自己四肢都弃我!”
参考书目(以汉文名首字拼音为序排列)
原始典籍及译本
阿闼婆吠陀集(Atharvavedasa Chita,梵语天城体字母本):
罗特(Roth,Rudol ph),波恩,1966。
阿闼婆吠陀歌咏(Hymns of the Atharva-veda,英译):
布隆姆菲尔德(Bloomf iel d,Maur i ce),德里,1987。
大正新修大藏经:
高楠顺次郎与渡边海旭,东京,1 9 2 8。
梨俱吠陀歌咏(Die Hymnen des Rigveda,梵语的拉丁字母转写本):
奥夫莱希特(Au f r ech t,Theodo r),柏林,1955。
梨俱吠陀(Der Rig-Veda,德译):
盖尔德纳,(Gel dner,Karl Fr ied r ich),剑桥(马萨诸塞),2003。
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
杜特(Du t t,M.N.),德里,2004。
摩奴法典(汉译):
马香雪(转译自迭朗善【A.Loi se l eu r-Des l ongchamps】之法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五十奥义书(汉译):
徐梵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 9 9 5。
印度格言(Indische Sprüche,梵文及德译):
波特林克(von B9ht l ingk,Ot to),圣彼得堡,1870—1873。
字典和工具书
波特林克:
简本梵语字典(Sanskrit-W9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圣彼得堡,1887—1889。
荻原云来:
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东京,年代不详。麦克唐内尔(Macdonell,A.A.)与凯思(Keith,A.B.):
吠陀名相索引(Ve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德里,1995。摩尼尔-威廉姆斯(Mon i e r-Wi l l i ams,Mon i e r):
梵英字典(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牛津,1899。
研究论著
阿贝格(Abegg,Emil):
印度和伊朗的弥赛亚信仰(Der Messiasglaube in Indien und Iran),柏林和莱比锡,1928。
奥博里斯(Oberlies,Thomas):
梨俱吠陀之宗教(Die Religion des Rgveda),维也纳,1998。
奥登贝尔格(Oldenberg,Hermann):
吠陀宗教(Die Rel igion des Veda),斯图加特和柏林,1917。
贝歇特(Bechert,Heinz)与希姆森(von Simson,Georg)主编:
印度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达姆施达特,1993。
基尔弗(Kirfel,Willibald):
印度人的宇宙观(Die Kosmographie der Inder),波恩和莱比锡,1920。
季羡林:
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辩机原著),中华书局,北京,2 0 0 0。
金克木:
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1 9 9 9。
天竺诗文(梵竺庐集【乙】),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1 9 9 9。
康勒(Kangle,R.P.):
考提利亚的政事论(The Kaut i līya Ar thaŚāst ra),孟买,1972。
拉森(Lassen,Christien):
印度古代知识(Indische Al ter tumskunde),莱比锡,1867。
罗特(von Roth,Rudolf):
四纪元的印度学说(Die Indische Lehre von den vier Wel tal tern),出自其短文集(Kleine Schrift),斯图加特,1994。
齐默(Zimmer,Heinr ich):
古代印度生活(Altindisches Leben),柏林,1879。
瓦克纳戈尔(Wackernagel,Jacob):
短文集(Kleine Schr i f t),哥廷根,1955。
韦伯(Weber,Albrecht):
印度研究(Indische Studien),柏林,1850[193]。
吠陀中关于时间划分和大数的陈述(Vedi sche Angabenüeber Zei t theilung und hohe Zahlen),载自《印度漫游(Indische Streifen)》第91—103页,柏林,1868。
(刘震,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与伊朗学系博士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