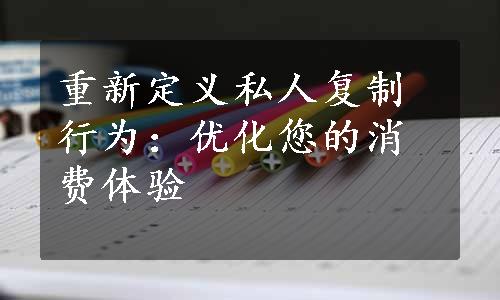
经前文分析,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制私人复制行为,只能由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和《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第24条第1款第1项推断出来。并且,通过该条的目的立法方式,无法明确判定某一行为是否为私人复制行为。笔者认为,随着数字技术背景下私人复制问题越来越普遍,我国应在合理使用制度中单独规定私人复制权,清晰地界定受合理使用制度保护的私人复制行为之定义。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定义的完善:
第一,用“非商业目的”对私人复制中的“私人”进行限定。受合理使用制度保护的私人复制行为必须具有“非商业目的”,而不再局限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目的。这种立法方式的着眼点是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关注社会公众和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符合应对数字技术时代新技术的核心原则。然而,“非商业目的”是比较宏观而笼统的限定,还需要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非商业目的”的含义进行具体阐释,细化的重点有两个:其一,商业性使用不等于造成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损害。虽然商业性使用关注的是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将两者画等号,即便是合理使用行为也会对著作权人的潜在经济利益造成轻微损害,故不能单纯从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损害来认定是否为商业性使用。其二,商业性使用应关注作品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一项资产在交易市场上的价格,它是买卖双方竞价后产生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18]是对一项资产价值的综合反映,一般不会因为少量的复制件的存在而波动。所以,倘若一种复制行为造成了作品的市场价值的波动,这种复制行为的严重程度必然达到了侵犯作者复制权的程度,就不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内的私人复制行为。
第二,对复制的定义着眼于是否具有独创性表达。随着新复制技术的不断涌现,我国立法中对复制行为的列举式立法方式已逐渐暴露其局限性。如前所述,我国《著作权法》对复制进行规制的着眼点是复制品的数量,并没有关注复制品的本质属性。如3D打印,原作品为2D作品而复制品却可能为3D作品,复制品并不是完全和原作品相同,如果应用我国法律条文“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则会产生争议。因此,建议着眼于复制品未增加任何独创性表达的本质特征进行立法,将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5项修改为:“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录制、翻拍及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固定在有形载体上而未增加独创性表达的权利。”[19]通过这种方式,复制行为的定义更清晰且适应数字技术的大环境,也同样规制了属于复制行为范围内的私人复制行为。(www.daowen.com)
第三,让私人复制行为的性质受作品合法性的制约。对于受合理使用制度规制的私人复制行为,我国法律并未要求复制作品的合法性。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考虑,如果不设置作品合法性这一限定条件,所有侵害作者权益的非法复制品就可以通过合法的私人复制行为传播和推广,这不仅会使作者的权益严重受损,也不利于遏制著作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因此,作品具有合法性一定是受合理使用规制的私人复制行为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私人复制因一些客观条件会判断力不足,不足以准确地辨别出作品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律不适宜过于加重私人复制者的判断责任,可以尝试使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即私人复制者在判断作品合法性时,如果通过一些外观要件和客观条件,有理由相信作品具有合法性,即便该作品不具有合法性,私人复制者也可以免除因判断失误而产生的责任。这种处理方式既充分考虑到私人复制者的判断能力,又对侵权行为起到了限制作用。
因此,建议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加入“私人复制合法性需以作品合法性为前提”的规定,但应降低私人复制者的判断责任,即作为善意私人复制者,只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作品的合法性即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