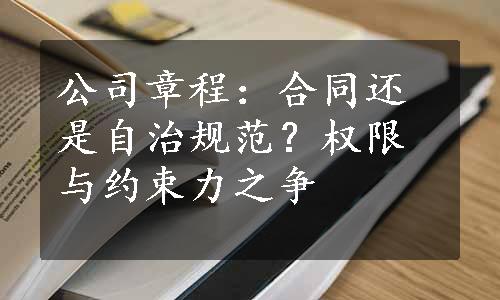
某有限责任公司有三名股东甲、乙、丙,分别持股40%、30%、30%,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是2017年6月30日,丙于2017年6月完成了实缴,但甲、乙一直未能全部实缴到位。2017年8月,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在甲、乙同意而丙反对的情况下作出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将股东出资期限延期至2018年12月31日。丙对此十分不满,但又因该决议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形式要件而无法否定该决议的效力,各方并未签订出资协议,亦无法主张违约责任,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是公司章程性质的自治规则说所带来的“恶果”。如果认为公司章程是合同则可以解决这一困境,但是又无法解释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力问题,这便是公司法上由来已久的公司章程性质之争。由本案也可以发现,公司章程的性质不仅是理论上务虚的表达,更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遗憾的是,现有的理论纷争多是泛泛地谈公司章程究竟为自治规则还是合同,但在实践中的公司章程,少则二十余条,多则数百条,所有的具体规则均为自治规则或者均为合同的表达是否失于粗疏?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使采取自治规则说,也要承认一些章程条款是具有合同属性的,至少是股东之间的合同,尤其是初始股东之间?即使采取合同说,也要承认一些章程条款纯属自治规则,与合同无关,即便不同意该修改的股东依然要受到章程规则的约束,而无须借助经济学上的宽泛合同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换句话说,能不能将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类型化,将公司章程的性质由一元论变成二元论?现有国内研究中,有学者提到了这一思路,如钱玉林教授认为,有必要对公司章程内容作类型化的分析,以便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的法律依据找到正当化的理由。作为合同的公司章程包括:(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3)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有一些公司章程条款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形来确定为合同还是自治规范,具体包括关于股东表决权、股权转让、股权继承、利润分配权的条款。如果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针对的是个别股东权,则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个别股东权予以限制或剥夺缺乏正当的理由,此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应以合同的方式进行。[1]
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并在两个维度上作出努力:一是将视角下沉,具体地研究公司章程的哪些条款应当作为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合同来对待;二是将对章程性质的研究从务虚走到务实,通过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来论证将公司条款类型化并进行二元论解释的合理性,以最大化回应实践的需求。下文首先对现有章程性质学说进行梳理,指出现有学说的缺陷或不足;然后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整理公司章程中常见的各类事项;接下来将这些事项进行二元的归位并阐述理由,当然重点阐述哪些内容应视为合同,剩余的则应归入自治规则范畴;特定情形下,还存在自治规则与合同相互转化的可能,需单独加以阐述;最后则是本文的结论部分。(www.daowen.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