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治所类城市因系官员衙署所在,是地方行政权力的重心,一般多有高大围墙和壕沟。即使没有大兵屯驻,亦至少有部分士卒把守。这类治城,一般多处水陆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往往也是地方上的经济贸易重心,商贾辐辏,粮财充足,不但可以固守,而且可以久持,因此,是最理想的避难之所。战火波及之处的几乎每一座治所城市,都接纳了大量逃难的人口,赖以活命者甚众。比如省城西安接纳人口就很多,仅北乡和西乡的回族逃入城内者就有千余家[92]。即使固原硝河城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战时避入城者高达六百余家[93]。礼泉县四乡小民战时亦大量涌入城中避难,时人邑儒学训导杨翰藻有诗记曰:
连日西隅已被焚,
城门启处窜纷纷。
车驱马骤何堪见,
女哭男号不忍闻。
赈恤深渐无善策,
藩篱暂幸避妖氛。
劫来更有关心事,
嘱吩胥役良莠分。[94]
杨氏亲历礼泉围城,仅用寥寥数语就把小民举家逃难入城时那种人车纷繁嘈杂、拥堵于道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避难救生的紧张慌乱之情跃然纸上。治城数量有限,有限空间之中包括衙庙、坛院、仓监等大量必备的公共设施[95],真正可供普通民众居住的地方并不宽裕[96],战时容纳新增人口的能力比较有限。对于大量远离行政治城的乡村人口来讲,那些离家较近且数量众多的堡寨,成为更好的避难之所。
西北小民自古即有修筑堡寨的传统,而这些堡寨在防盗御寇方面也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见图5-2)。堡寨最初皆为具有极强军事性质的小城[97],于用兵扼要设守之处堆土垒石或树栅为墙,故“有堡之处皆有墙壕围护,如城郭然”[98]。西北地处边陲,域内堡寨遍置,以利攻防,古已有之。及至乾嘉,西域纳尽化归,陕甘已成内地,堡寨原有军事职能丧失,遂或废弃,或为民居[99]。部分有人聚居的堡寨,修葺如常,基本形制完备,防卫功能依然存在,足资御寇自守。如肃州众多堡寨,皆系嘉靖修筑,当时务极坚深,入清后民仍得其利[100]。又如古浪之大靖、土门等巨堡,民户皆有数千,城高池深,商务繁华,丝毫不亚于治城[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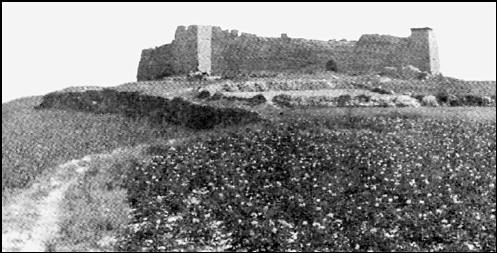 (https://www.daowen.com)
(https://www.daowen.com)
图5-2 兰州附近废弃的乡间避难堡城
(资料来源:王建平编著:《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
同治战前,陕甘两省堡寨众多,分布广泛,几乎无县无之。如庄浪县有8个堡寨[102],山丹有34个[103],平罗县多达64个[104],而西宁卫所统领的堡寨数更是高达99个[105]。堡寨有自为一村者,有下辖数村者,有堡下辖堡者[106],亦有称为总堡者,如西宁卫之南川总堡、北川总堡、猪儿沟总堡、沙塘川总堡等,每个总堡都下辖一定数量的村、堡、寨[107]。从这种情况推测,辖村庄的堡寨应该是由多个小的自然村落组成的区域中的一个中心村,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行政村,可能承担着一部分行政职能。
这些以治城为中心零星散布有坚固围墙的堡寨[108],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趋于离散,空间可达性较好,遇到险情比较容易躲避。对于乡居的普通民众来讲,就近迁往人口更多、建有围墙可资防守的堡寨,除了可以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外,或许也可以得到某些实际的安全保证。而地方士绅及致仕乡居的官员则把筑堡练团,坚壁清野,视为御寇自保良策,极力倡导。“于已筑之堡,随时补葺,勿致倾圮。于应筑之堡,悉力兴修,务成觕角。设再有警,即将财物牲畜尽数入堡相保守,不惟我有所据可恃无恐,且使寇无所掠不战自去矣。”[109]这些已有或新筑的堡寨,有不少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小民赖以活命的处所。比如抚彝厅的古榆寨,又称大鸭翅堡,在县东三十里,“同治六年监生申大儒、张承郿等人捐资重修,同治兵燹,全活甚众”[110]。
相对于散布乡村的堡寨,治所城市的战略位置和政治影响力更大,回军攻城的目标更明确,官军守城的态度也更坚决。以关中西、同、凤三府为例,战争期间,户县、临潼、咸阳、兴平、蓝田及朝邑等20余个治城均遭不同程度袭扰,同州府城及蒲城县城均围攻七八昼夜[111],醴泉围城两月之久,省城西安、凤翔府城及岐山县城等更是遭围城长达一年数月之久。但治所城市城墙高大(见图5-3),防守人员众多,武器也较精良,相对于一般的堡寨,安全性更高,最终多获保全。真正被攻破的治城极其有限,仅渭南、高陵、泾阳、华州、华阴及韩城等数座而已。其中韩城攻入即被驱离,并未真正占领;泾阳围城六个多月,占据仅十余天[112];只有高陵一城,从同治元年五月中旬破城,到同治二年九月撤离,前后占领长达一年四个月之久[113]。因此,小民逃入治城者,多得活命。临潼行者桥有北、东、西三个堡子,战时各堡人逃难方式不同,结局亦不同。南堡人多逃往县城,幸存者较多,而北堡人则就地躲藏,多遭杀戮[114]。

图5-3 循化厅高大的城墙
(资料来源:王建平编著:《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第136页)
然而,视线如果转向甘肃,我们就会发现,对于修有高大城墙且防守力量较强的治所城市来讲,所谓安全性,其实也是相对的,整个同治战争期间,甘肃有大量治所城市被攻破,人口损失相当严重。比如镇原县战乱期间“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先后入城避难,其守城最得力,其历时亦非久,久则怠矣”。同治七年三月初九日,县城被攻破,城内及逃难人口大部被杀,县志称,其时“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115]。还有一些记载更为触目惊心,比如固原州城,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被攻破后,史称“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116]。同治二年八月,平凉府城被攻破后,光绪《甘肃新通志》记载称“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117],劫难之后统计,全城“仅存百四十七户”[118]。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攻破,“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119]。除了府州治城,史料中记载的部分县城人口损失亦相当惊人,比如靖远县城,同治五年城破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120]。而狄道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攻破后人口损失居然也高达十余万众[121]。随便翻检一下,不难发现,有太多与同治西北战争有关的论著,都不加分析地引用了这些记载,并当作信史,以此说明同治战争之残酷,以及战时人口损失之惨重。
但是,根据现有研究,经简单推理,就会发现,这些记载的可信度不高。同治以前,西北地区治所城市人口的真实规模,普遍较小,很难支撑这样的说法。以清代西北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西安为例,在同治战前,其人口最多不过十余万[122],兰州城的人口更少,宣统“地理调查表”汇总数据显示,宣统年间,甘肃省城兰州城内人口尚不及1万,即使算上关厢及附城西川人口,总数也不到6万。甘肃人口第二多的城市秦安县城,其数不过3万余口[123]。战时甘肃虽然全省处于战火之中,但省城兰州并未受太多攻伐,虽然因饥疫造成人口亦有损失,但战时也接纳相当多的逃难人口。秦安的情况类似,整个秦、阶一带,战时受影响较小,不但人口损失不多,而且还有逃难人口迁入。因此,这两个治城,同治战前的实际人口应该不会比宣统调查的人口多多少。即使是最大胆的估计,人口翻倍,同治以前,作为甘肃首位度第一的省城兰州,其人口也仅10万出头。
平凉商业素称发达,有肃东“旱码头”之称,户口繁盛,亦是回族集聚之所。而平凉府城,城高池深,规模也相当大。虽然如此,但要说其人口比兰州多至数倍,有数十万口之众,则不太可能。据民国《平凉县志》记载,同治二年春回军围攻平凉,“至八月十二日用地雷轰陷之,全城丁口十三万余,殆尽焉。自是厥后陇上城郭无完土,闾里绝烟火,田野遍蒿蓬者几十载,孑遗之氓百千不一存,呜呼,惨矣!”[124]县志与通志所记,一个十三万余口,一个数十万口,两者相差甚多。从新中国成立后统计数据看,平凉城区不过10平方千米,1953年城区人口仅有6.2万,1985年也不过7.9万[125]。基于这些基本的史实,很显然,即使考虑到战时大量小民入城避难,平凉城破后人口损失数十万也是不可能的。而靖远、狄道这些蕞尔小城人口损失十余万,显然更是无稽之谈。这些记载,多出于民国时期所修的志书与个人文集,可能为道听途说、街谈巷语之词,亦或如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类文学修饰之语。
不过,此类个案记载虽多夸张,但战时甘肃治所类城市被攻破后人口损失惨重也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合水县城被攻破,“人民杀毙死者十有六七,是年七月十二日,城又陷,贼由东城壕入,人民逃尽,止余空城。八年七月知县廖绍铨到任,多方召集,城内只有二三十家”[126]。被攻破的治城,大多人口凋零若此。正是基于这种治城更加安全的普遍共识,战时大量小民麇聚其间,一旦城被攻破,人口损失更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