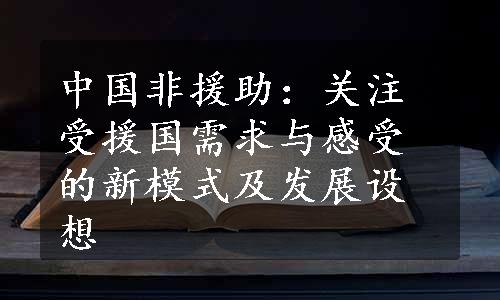
不同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对外援助延续“宗主国”的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拥有反抗殖民主义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样肩负着自主发展的时代任务,因此中国对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一直秉承尊重与信心。进而,中国对非援助在实践行为上也表现出关注受援国心理感受、契合受援国发展需求的新型模式。
(一)主动与受援国发展战略对接
关于国别援助政策的制定,西方援助国为体现权力的意志,从自身角度设计援助方案,遭到了非洲国家的反感。冷战结束初期,“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援助国以腐败和政府治理能力低下为由严厉批评非洲国家政府,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之所以不能帮助其实现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国家的政府贪污腐败、监管机制不健全。基于此,西方国家援助重点在于推动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此后,西方发展援助开始大规模推动附带条件的援助模式,特别是政治条件,重点推进“第三波民主化”。这种强势的做法遭到非洲受援国的强烈不满,导致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恶化。西方援助国不得不转变援助方式,不再那么直接,而是要求受援国按照其意志制定“减贫战略文件”(PRSP)来申请援助。以坦桑尼亚为例,OECD/DAC援助国通过指导坦桑尼亚制定PRSP,将其发展理念强加其中,随后再按照PRSP协调DAC国家对坦桑尼亚的援助政策和领域的设定,这其实削弱了坦桑尼亚政府的自主发展能力。因为坦桑尼亚政府希望优先振兴民族经济,而DAC援助国却不置可否,将改善政府治理设为援助的优先选项。这迫使坦桑尼亚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援助国的支持。
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援助将对受援国主导权的尊重贯穿始终。在制定国别发展合作政策时,中国充分尊重受援国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上的主导权,确保对非援助政策与受援国发展战略精准对接。在充分调研每个受援国发展需求以及区域整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中国及时修订《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规划纲要》,统筹考虑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安全等对外战略,对中长期援外目标任务、投入规模、资金结构、空间布局、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等做出系统安排。同时,根据受援国对中国主动提出的援助诉求以及中国自身的援助能力,制定《国别援助指导意见》以及“国别援助项目库”,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与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行对接,一国一策,因国施策。在项目的准备阶段,中国与受援国的中央政府、项目所在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各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以全面掌握其对项目的设想与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在项目的建设和执行阶段,中国努力动员受援国的政府、企业以及当地居民广泛参与,在各个实施环节中注重提升受援国独立开展项目规划、执行以及管理运营的水平。此外,从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可以看出,中国努力确保受援国相关方参与项目设计的模式也是援助项目顺利进行的有效保障。
仍以坦桑尼亚为例,为了吸引中国援助进入本国优先发展领域,坦桑尼亚采取了三大步骤:首先,坦桑尼亚政府于2000年颁布了《国家发展愿景2025》,明确提出了总体发展目标是将坦桑尼亚由最不发达国家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其次,坦桑尼亚政府于2011年颁布了《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了基础设施更新、农业改革、工业增长、人力资本和技能提升以及旅游、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发展等五个优先发展领域。最后,基于两大发展规划,坦桑尼亚政府积极与中国沟通协调,主动提出“加强港口设施、改善中央铁路走廊和支持光纤网络项目”等系列发展设想。中国政府尊重坦桑尼亚的发展诉求,结合自身的援助能力,为坦桑尼亚援建了包括光纤骨干网在内的一系列项目,改善了坦桑尼亚的营商环境,推动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注重提升受援国的生产能力
西方援助国出于殖民主义的历史渊源,援助较少关注与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领域,不仅弱化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反而强化了其对援助的依赖。西方学者瑞德尔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对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后殖民时代,外援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新关系延续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各种老关系”。[41]多斯桑托斯则认为,西方援助之所以不支持受援国的工业发展是希望受援国能够利用援助资金购买援助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这些产品的价格是高度垄断状态下的产物,是国际市场上任何买主所不敢问津的”。从而形成了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依附”,出于避免受援国利用资源禀赋与其形成竞争的考虑,因此西方援助不可能真正根据受援国的发展需要进行,长此以往就导致受援国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使它们在经济上长期地依赖于援助国的援助”。[42]
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启动对非援助之初就注重提升受援国的生产能力,旨在提升受援国自身的造血能力。周恩来提出,中国援助既要满足受援国的眼前急需,也要关照受援国的长远发展,因此“要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使工业援助与农业援助相结合”。[43]这种援助直接支持受援国工业发展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分罕见,并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也鲜有西方国家涉足。
基于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帮助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设了工业项目,奠定了受援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例如,几内亚卷烟火柴厂项目、赞比亚姆隆古希纺织厂项目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了多哥糖联等一批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大中型项目。再如,1981—1983年中国在赞比亚铜带省建立了钦戈拉玉米磨粉厂,年产量6万吨,减少了铜带省和西部省精玉米粉的进口。[44]此外,中国还应非洲伙伴国的要求参与发展合作项目的后续运营,以帮助当地提升运营管理能力。从1985年起中国开始对援卢旺达马叙塞水泥厂项目实施代管经营,由中国企业派遣中高层管理者以及核心技术工人负责生产经营并在各个管理和生产环节培训当地人员,在五年合同期内全部收回投资并上缴利税,而且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实现年产量大幅提升,赢得了卢旺达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誉,仅代管合同就延长了四次。[45]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以优惠贷款模式大规模资助了一大批生产性项目。1996年中石油在苏丹建设石油开发项目,由中国优惠贷款资金支持油田开发和输油管道建设。建成后,中石油与苏丹、印度等国家企业组成“大尼罗石油公司”进行管理经营。1999年8月第一批60万吨石油出口,结束了苏丹石油进口的历史。之后,中石油帮助苏丹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使苏丹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迈向了工业化。石油出口不仅为苏丹赢得了发展经济急需的大量外汇,还带动了电力、交通运输、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发展。此外,中石油在当地雇用了6000多名正式的苏丹员工,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外溢和转移。中国对苏丹的优惠贷款支持使得苏丹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成了发展优势。中国帮助苏丹建立起包括石油勘探、生产、炼制、运输、销售的全产业链,使苏丹从石油产品进口国迅速转变为石油出口国。相比之下,尼日利亚在英荷壳牌公司等西方石油巨头的主导下开采石油长达50多年之久,但至今仍未建立起完整的石油生产和加工体系。中国援非的生产类项目涵盖能源、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方方面面。时至今日,中国援建的多哥糖联、刚果(布)水泥厂等一批项目一直保持盈利,在促进受援国生产和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还从自身的发展经验出发,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洲的互联互通及营商环境的改善。相关项目改善了受援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受援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援助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分离
冷战结束后,OECD/DAC援助国为了推动受援国按其意志进行改革,大规模推行一般预算支持(GBS)的援助模式,即:将援款直接打入受援国财政账户,同时附带一系列改革指标,并派出专家组进行监督和评估。这种援助模式产生的消极影响包括:一是效率低下。援助国为了监督资金的使用,组成了几十个监督委员会。而受援国也不得不派出大量政府官员与这些委员会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造成了大量行政资源的浪费。OECD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受援国每年要接待来自各援助国近300个代表团,花费高达50亿美元的资金成本。有些受援国每年需要为800个援助项目做准备,并撰写2400份援助项目报告。二是援助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极力掩盖受援国存在的问题。GBS极易造成腐败,而援助国为了自身的形象和利益,往往帮助受援国官员掩盖丑闻,这其实是对腐败的进一步纵容。为了监督GBS的使用情况,援助国雇用了庞大的专业团队、形成了“援助行业”的部门利益,双边援助机构如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有近万名员工、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雇员超过2万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也员工数千,多边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也有过万员工,这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由精英人士组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46]这些人以发展援助为事业,“进”可以在多双边机构中实现流动和上升,“退”可以在本国外交领域大展其才。这使得他们将保持援助项目的持续性作为职业生涯的首要任务,而非其对外宣称的确保援助的有效性。即便发现了受援国系统出现了援助资金滥用和贪腐行为,他们也会出于保住自己饭碗的立场,使用各种手段使例行的评估工作表面化抑或直接掩盖,这无形中推高了受援国的腐败风险。例如,2018年底在英国、德国等主要出资国的压力下联合国启动了对其援助的“乌干达难民援助计划”的调查,结果发现超过百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被乌干达当地非政府组织滥用。作为该项目的前四大出资方英国、德国、欧盟和美国对此纷纷表示撤回资金、起诉责任人。[47]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开始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对财政援助进行反思和批判。有学者选择具体受援国进行案例研究,来评估财政援助的效果。如拉维和谢费尔以埃及接受财政援助的情况为研究对象,发现受援国在接收了大量援助资金后并没有全部落实到援助项目中,而是助长了相关利益群体的消费,使得受援国国内消费水平上升。而为了维持这种消费上升趋势,在财政援助减少时受援国政府转而采取了举债的方式,“这就会导致债务负担和通货膨胀等问题”。[48]另一些学者则直接对财政援助方式进行批评,例如,艾泰认为英国采用的财政援助只能使得受援国少部分利益群体获益,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不足。[49]
相比之下,中国则主要采取了“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相分离的方式。在为非洲国家援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医疗和农业技术合作、派遣教师以及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时,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中方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和拨付。除了少数向对方政府提供的现汇援助外,物资赠送也是由中方负责组织采购和交付。特别是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援外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为提升非洲受援国的项目实施和管理能力、推动援助“本地化”,中国积极将受援国相关人员纳入各实施环节,但是资金管理始终由中方直接处理。此外,中国实施企业具有人员和物资成本的价格优势,极大地保证了援助项目的质量和效率,使同样数额的援助资金能够比西方国家办更多的事情。
专栏14——缘何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2018年4月18日下午,新组建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揭牌。
作为新成立的部门之一,且与国际工作、外事工作联系紧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在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时就吸引了大量关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www.daowen.com)
4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一则国务院任免消息,任命王晓涛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公开报道显示,他此前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宋微,从学者的角度介绍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前世今生”。
呼吁已久
此前援外事务由“部际协调机制”进行管理。宋微介绍,机构改革前,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是由“部际协调机制”进行宏观协调和管理,核心为商务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三家,由商务部担任组长,另两家单位担任副组长,其他成员包括40余家部委和相关单位。具体落实工作则由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负责。
在此机制下,无论是从商务部角度的平行协调,还是从对外援助司角度的下对上协调都存在一定的难度。此次机构改革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定位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使得上述协调问题迎刃而解。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以上三个部委以外,还有其他部委承担和管理一些对外援助事务。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援外医疗队的选派和管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与多边开发银行的联系;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优惠贷款项目;科技部管理中国对外科技援助工作等。地方也有管理对外援助事务的职责。
各省区市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一定的对外援助管理工作,除了协助商务部做好相关工作,还要参与属地企业的相关对外援助项目管理、对外援助实施主体的监管等。
中国的具体援助工作深入受援助国国内,一般由驻外使馆经商处或中国派驻受援国的经济代表处负责。
适应趋势
使各领域援助举措能在受援国形成合力。谈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的背后,宋微还强调称,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组建是为了适应当前国际发展筹资格局变动、精准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而设立。
她表示,当前以“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增长乏力。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国会要求削减对非援助预算;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发展工业化,对外部发展资金的需求增加。
这就对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援助资金的使用必须力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现有对外援助资金来源,提高援助效率。
宋微称,总的来说,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宏观层面,可以优化对外援助的顶层设计,使其充分反映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利用援外资金配合“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落地;在中观层面,可以更好地协调农业、卫生、教育等各专业部委的对外援助工作,使得各领域援助举措能够在受援国形成合力;从微观层面,可以更深入地调研受援国发展瓶颈和诉求,从而为其量身打造差异化的发展方案。
此外,从大国外交角度看,陈须隆认为,“和平和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帮助和援助,这需要通过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来落实。
宋微还表示,从国际发展援助趋势看,项目援助(CPA:country programmable aid)已成为主流,即:为受援国制定未来3—5年的重点发展目标,以此为中心,综合设计援助内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未来一定会在突出重点、综合规划援助方案、避免“碎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2018年4月19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