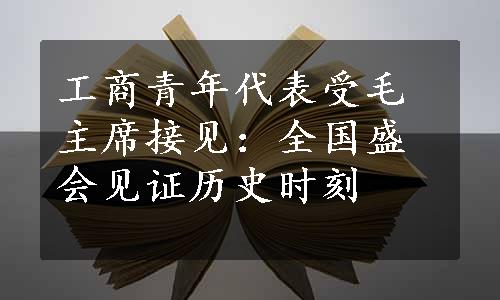
加工订货的模式,不是每个工商业者在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愿意接受的,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打字机供不应求,生产厂家急剧增加,市场非常好。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和改造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加工定货的利润比较薄,我为什么愿意继续接受加工订货并且接受包销产品的条款?因为企业在“五反”时期遇到困难时,股东老板纷纷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苦苦支撑,但厂里工人都支持我搞下去,他们也知道我把金首饰都卖了应付开销,所以主动表态工资可以晚点发。卢湾区团委书记施惠群找我谈话,勉励我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把厂办下去。政府也及时调整措施,扶助企业发展。这些经历都在潜移默化促使我转变经营理念和人生价值观。我想,只要企业有利可图,能够维持下去,把产品卖给国家有啥不好?所以就接受了市文化用品公司的订货包销,每月30台。那时,一台打字机的市场价为625元,我卖给国家贸易公司,只要340元。同行因此都在骂我,但我不为所动。我已经懂得,我们是新中国的一分子,不能局限于一个小的自我当中,应该爱自己的国家,个人利益要和国家的利益相结合。340块钱的收购价虽不高,我经过成本核算,还有合理的利润空间,我们怎么能够在国家的头上赚取暴利呢?同行中,我的厂是第一个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的。当时连我的合伙人都埋怨我说,你就是要出风头,就是要当人民代表,才这样做!但我厂里的党员、团员都支持我。说起党员,我们厂里的第一位党员,还是我到政府要来的,我那时主要管对外业务,厂里的职工福利、劳资协调,由合伙人负责,结果钱花了不少,用的却不是地方,职工意见较大,劳资纠纷常常有,工人之间也会有争吵,经常为了这些事要我出面开会调解,烦得不得了。我就去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他们给我派一个共产党员,派一个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们厂搞工会工作,协调好劳资关系。他们都奇怪,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工商业者?后来真的派来了一个人来当工会主席,我们合作得很好。
那段时间我经常参加区民主青年联合会的活动,民青联很重视我们,经常组织学习、组织活动。我在1953年出席过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代表大会,当时青联有“小政协”之称,集中了各方面的青年代表,共同特点是要求进步,建设新社会。
接下来要搞公私合营,我打了几次申请合营的报告,答复全是条件还不成熟,要创造条件。组织我们参观学习已经合营的厂家,比如刘公诚的水泥厂。刘公诚是刘鸿生的儿子,解放前是秘密党员。经过参观了解,我发现公私合营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合营后,企业内劳资矛盾没有了;第二是不用忙于“轧头寸”(调配资金)了;第三是工商业者的职务有保障,厂长还是厂长;第四是采用“四马分肥”的办法,经济收入有保障。那时候,工商界有一批年轻人非常积极。(www.daowen.com)
迎接大合营时,我们在瑞金二路49号卢湾区工商联开会,参会人员大概有100人左右。区里一位民青联干部推推我,暗示我上去表态。我就跳上台去,倡议成立青年突击队,帮助各家商户清产核资,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啊。我们建立了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支青年突击队,以后全面铺开,各区都搞起来了。当时区工商联条件很差的,开大会连凳子都要自己搬。开会印通知、发通知、写标语等,都是自己动手。1956年1月2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大合营那天,大家涌到中苏友好大厦开会,敲锣打鼓送申请书。我作为工商青年代表,被安排坐在前排工商联常委的位置。会场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要求上台发言的人排成了长龙,我被一名工作人员拉到边上,做了个录音发言,内容大体是讲自己激动的心情以及今后要如何努力工作,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1956年2月,上海组成了60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陈铭珊任团长,我是副团长。会议开了八天,讨论十分热烈,另外还安排了许多参观、联谊活动。上海代表团特别庞大,既有老板,也有私企从业人员代表。上海代表团在文娱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不管唱歌跳舞还是唱戏都轻松自如,但在植树劳动中却出了“洋相”,铁锹不知道如何拿,远不如兄弟省市的工商业者动作熟练。大会将结束时,上海代表团推派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之雄(她父亲是有“化工大王”“国货大王”之誉的方液仙)上台读一份倡议书,号召工商业者争取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她还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上台用普通话宣读,真好听。后来才知道为了读准发音,身为北京人的玲奋机器厂副厂长王兆五特地为她作辅导。毛主席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