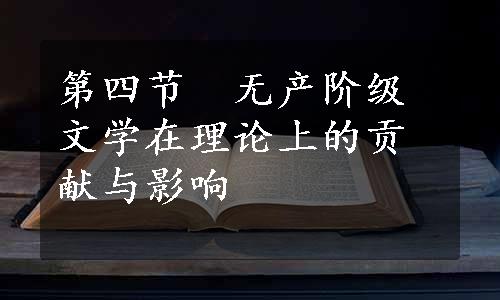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在日本流产了,除了日本当局推行法西斯主义,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学阵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学家缺乏坚定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够深入理解而产生动摇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学同政治运动紧密相连。从日本传统文学和整个日本人审美情趣来看,“主情”(72)、“超政治性”(73)、“感物兴叹”(74)、追求“风雅”(75)境界是他们一贯推崇的文学主张。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在日本缺乏牢固的生长根基。这也就导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些局限性。尽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没能在日本旷日持久地扎下根来,但作为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一环来说,它不仅推动了文学的进步,而且在理论上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像无产阶级文学那样强调文学理论的建设。
当然,文学理论的建设总是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联系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确立和建设中,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德永直、宫本贤治等人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是他们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发展。应该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发展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展息息相关。关于他们对理论的重大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定位。
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伊始阶段,平林首先就发表了一篇称为理论性或纲领性的文章——“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播种人》1922.6)。他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唯一纲领。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应该和大众协调一致,离开人民大众的运动是徒劳的,要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文艺运动必须是一场阶级战斗,而这场战斗不是单纯的观念与观念的战斗,在其背后存在着利害与利害的对峙、权力与权力的相持。因此,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的、艰苦的、充满困难的运动。他号召无产者要以满腔的热情,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76)。平林的理论是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上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要和反抗资本家、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随后,青野发表了“革命者的艺术”(《艺术战线》1922.10)和“阶级斗争与艺术斗争”(《播种人》1923.2)的文章。他说:“我们所迫切期望的、已经在日本布满荆棘的土地上发芽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是以革命者创历史的生活气氛为基调的艺术。它是革命者的艺术。”(77)他还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战斗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要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战斗。背离了这一点,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将无任何意义(78)。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论主张,使无产阶级文学从诞生起,就和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解放事业融为一体。因此,无产阶级文学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目的意识论”。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目的意识论”源自青野的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他分别于1926年9月和1927年1月在《文艺战线》杂志上发表了“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和“再论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的文章。
在“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平林关于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关系的论点,他主张把目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当中。他首先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不同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产生,描写日本无产者的生活、表现他们的希望与要求的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无产阶级文学是随着无产阶级自然生长、文学创作者(79)的表现欲也在自然生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不是文学运动。他说:“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因为它在自然生长的基础上产生了目的意识。没有目的意识,就不可能有运动。”(80)有了目的意识,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已经成熟和深化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职能就在于要把无产者的自然生长引向目的意识上来。显然,他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引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方向。
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艺术,青野在“再论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一文中,一方面继续强调自然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学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目的意识需要由社会主义意识来统帅。他说: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学中灌输社会主义的(真正整个无产阶级的)目的意识。换言之,必须批判、整理在自然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中所出现的诸种意识形态的混入——事实已经证明其中不仅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混入、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混入,不,甚至还有中世意识形态的混入——把它们组织到社会主义的意识中去。可以说这就是进入第二斗争期的任务。(81)
他十分坚信列宁所说无产阶级的自然生长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如果对无产者所表现出的不满、愤怒、憎恶等情感置之不理,那么绝不可能对他们的思想意识加以充分的批评、整理和组织。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部注入进去(82)。同时,他还对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要求。他说:
既然它是文学作品,那么就必须诉说人类——无产阶级——的感觉和情感。这如同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吃东西一样,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事实。我虽然要求无产阶级作家把握目的意识,但并没有说要无视文学的规则。(83)
在此,青野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形式应该多样化。他反对限制无产阶级文学题材。他清楚地意识到当今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进入了政治阶段,如果仅仅以政治斗争的舞台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话,将失去文学的真正意义。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政治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的政治暴露不是狭义的政治方面的斗争和暴露,而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不能要求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题材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斗争。
青野的“目的意识论”提出以后,《文艺战线》立刻做出了积极反应。林房雄根据青野的理论核心于同年2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明确指出大众自然成长的、无意识的行动要靠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去指导,文学创作要把握真正的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要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作家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文学创作,追求美的艺术价值。林房雄在文章中强调说:“我们坚信在阶级社会中的美的概念各个阶级不尽相同。我们所追求的美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美。颓废阶级、反动阶级的美绝不是我们的美。”(84)可以说,他们所提出的阶级艺术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充分意识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我们可以得知人类在社会中的实践活动是多样性的。人所改造的具体感性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也是多样性的。美是我们人类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一种能动活动以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和对象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美是一个感性具体的存在。它一方面是一个合规律的存在,体现着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又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所以,美是包含或体现社会生活本质、规律,能够引起人们特定情感反映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85)美具有客观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都应该有它们的美。但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美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它应是体现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相一致的阶级的实践、生活的产物。”(86)先进的阶级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只有先进阶级的社会实践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此,对于先进的无产阶级来说,一切反动阶级的“美”正是他们所要摈弃的。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
关于这个问题,在本章的第三节已经有所论述。在此需要补充的是,藏原惟人在“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1928)的文章中,首先是在同以往的观念主义作了对比之后来考察、规定现实主义的。他指出:如果艺术家对现实抱有一种先验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改造现实,并加以描写的话,由此所产生的艺术就是观念主义的艺术。反之,如果艺术家对现实不抱有任何先验的、主观的观念,以现实为现实进行客观描述的话,那由此产生的艺术就是现实主义的(87)。归纳其特点应该是:“观念主义的艺术是主观的、空想的、观念的、抽象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客观的、现实的、实在的、具体的。一般可以这么说,观念主义是正在没落的阶级的艺术态度,而现实主义是正在兴起的阶级的艺术态度。”(88)其次,他在文章中又对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进行了对比。他指出:浪漫主义是正在没落的地主阶级的文学。作为正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常常表现的是空想的、观念的、传统的。而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而登场的自然主义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的。其宗旨是回归现实、打破旧习、解放个性,不加粉饰地客观地描写现实。尽管如此,他也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本身带有明显的历史极限性。无论他们在客观描写方面作何种努力,他们都会给其现实主义带来一定的极限。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使命仅停留在个人的解放。自然主义的文学也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种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不代表社会的整体(89)。作为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时常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中摇摆不定,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搞调和主义,在思想、道德方面掺入了博爱、正义、人道等内容,但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还缺乏真正的认识,他们的文学还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90)。
通过藏原对上述观念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才不是停留在个人问题上,它不满足偶然的个体现象和抽象问题,更反对把社会问题归结到个体的本性上,它强调用社会的观点去观察所有个体的问题。
根据藏原的理论,完全可以归纳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无产阶级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始终是客观的、现实的。无产阶级抛掉了所有的主观成分去观察、描写现实。二、在同样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上,只有无产阶级作家用客观的、历史发展的眼光去观察社会,把握现实的整体性。三、无产阶级作家有鲜明的阶级观点,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前卫的眼”观察、描写世界。四、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主题突出反映解放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题是主要反映人的种种欲望,小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题则是歌颂社会的正义、博爱等(91)。
在题材方面,藏原也指出了无产阶级作家不仅仅限于以无产阶级为题材,而是包括现代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同时,在谈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对过去的现实主义继承方面,他特别提到了对现实的客观态度。在此所说的客观态度“绝非是对现实——生活无差别的、冷淡的态度,也不是超阶级的态度,而是以现实为现实,没有任何主观结构,毫无粉饰地加以描写的态度。”(92)
可以说藏原这个理论的提出对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在他的理论引导下,小林多喜二以其实践者的身份登上了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坛,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从此,“纳普”确立了“政治的首位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两大概念。
当然,也需要注意藏原的理论在分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他只看到了这两者的对立面。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上来看,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对立:一个对现实尤其是庸俗丑陋的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反感、主张创作自由、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偏爱表现主观的理想,另一个主张遵循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的创作原则、重视描写的真实性、反对抽象和空想、摈弃一切雕琢与粉饰的手法,追求事物的客观性。但是,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并非都是悲观主义、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一面,它也有乐观主义、革命的、积极的一面。积极的浪漫主义在于提高人的尊严感,唤醒民族的觉醒,促进人类对自由独立的要求。也正如高尔基在《我怎样学习写作》中所说:“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人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93)而作为现实主义来说,它也有另一面。这就像法国现实主义派大师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那样,他们的思想常常带有另一面,那就是艺术的真实不等于自然或现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要通过典型化或理想化来表现。关于这一点,巴尔扎克是这样说的:“在现实里一切都是细小的,琐碎的;在理想的崇高境界里一切都变大了。”(94)显然,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都是把生活中同类人物的特征加以集中提炼、概括化和理想化之后,才创造出一些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性格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浪漫主义的一面。由此可以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应该是完全割裂的、矛盾的。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也不应该取其一而废其他。就此,高尔基已经断言:“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95)藏原只把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重点放在了现实主义上,而忽视了无产阶级文学还需要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统一在一起,才能创作出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更为优秀的作品来。
尽管如此,藏原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丰富发展了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给“纳普”作家们很大的刺激和影响,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新纪元。
第四,关于“艺术大众化论”。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两派并立时期,曾经就“艺术大众化”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有关论战的具体内容第三节已经论述,在此不再赘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论战中,藏原惟人能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于1928年先后发表两篇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即“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新阶段——向艺术的大众化和全左翼艺术家的统一战线迈进”和“艺术运动所面临的紧急问题”。这两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要创造大众所理解、喜爱,并将其感情、思想和意志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无产阶级要走向工农大众,对他们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
大众化的文学要求艺术家在创作中本着为工农大众创作、反映其真实情感的精神,时刻考虑所创作的艺术作品能否被他们所接受、所喜爱。大众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要通俗化,也就是“教育者、启蒙者如何运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形式,包括旧形式,去在文化水平很低的工农大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96)。这在当时的日本,只靠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很难实现。因此,藏原也充分意识到文学的大众化要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正如鲁迅所说“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97)
最终经过多回合的论争,在统一战线内部对藏原的“艺术大众化论”基本上达成了统一的思想认识,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现阶段,其“艺术大众化”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艺术的大众化在拯救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同时,也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虽然在内容与形式问题上大家还不完全统一,有些机械,但在以后无产阶级文学出现的形式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藏原所论述的艺术大众化的问题,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迈向新的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在他的理论倡导下,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者积极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将文学创作直接面向工农大众,为以后无产阶级文学向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方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五,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方法论”。
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方法论主要是来自藏原惟人所提出的论点,即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1931年10月,他以笔名谷本清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他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提出这一理论的。
首先,他要求无产阶级艺术家创作文艺作品时,要描写反映阶级斗争的积极主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的主题始终是围绕着阶级斗争的,而阶级斗争是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它无处不在。因此,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者在面临这些情况时,必须始终从唯一正确的革命的观点出发,选择和描写具有积极意义的主题。
其次,他提出文艺创作方法要具有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例如,在关于“阶级分析”方面,反对只把它限定在理论分析上,要注意看作家对现实的理解,在此就向无产阶级作家提出了要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问题。在关于“阶级需要”方面,反对把它限定在当前运动的每时每刻中,对一切从属于阶级需要的问题不能进行如此单纯地理解,否则后果不可挽回。关于“人类情感”方面,反对将人类情感同人的义务的观念加以对立。因为在现实中,人类的情感往往会随着生活、思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一旦在现实中人类的思想、感情、意识等出现了矛盾也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关于“阶级义务”同“个人情感”的关系方面,同样反对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因为它们之间本身不存在任何“悲剧的分裂”,“个人情感”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固定不变的,“阶级的义务”也不是僵硬的、机械的。关于“典型论”方面,藏原说:
属于同一阶级、同一职业、同一年龄、同一性别、同一环境、同一意识等等的人必须在充分考虑更为具体的差别之后,进行艺术地概括,由此创造出艺术的典型。……
但是,无产阶级作家并不是毫无差别地可以描写存在于现实中的所有类型。从时代发展的观点上来看,他表面上只挑出那种多少有意义的类型,可以把其余的放在背面。(98)
这里所说的“典型论”是着眼于现实中正在形成的类型,并将现实中所找到、所发现到的类型进行艺术概括。它实际上是一种“类型说”。类型说的重点在于普遍性,它没有个性的特点。因此,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仅仅是真正含义“典型”理论的一个开端。不过,从现实生活出发、艺术地概括典型问题也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值得注目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文艺应从具体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公式概念出发的问题,也就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99)。他们的“典型论”概括起来就是典型要与个性相统一,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有内在的联系,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典型问题实际上就是艺术的本质问题,就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典型化,就没有艺术。”(100)尽管藏原的“典型论”还存在着缺陷,但他为日本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内容。
再者,就现实与艺术上的偶然和必然问题,藏原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者把现实过程中的偶然和必然联系在一起进行文艺创作,发现必然描写必然是无产阶级作家的本职,但对事物的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的偶然也必须视为全过程的一种动机加以观察和描写。
藏原的这一理论的发表,在当时的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不仅把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日本文学形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101)。
第六,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除了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外,还特别强调文学的党性和社会主义精神。从阶级属性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属于无产阶级文学。它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别。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1868—1936)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32年5月29日俄国的《文学报》上的一篇社论,名叫“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同年秋季,斯大林接见俄国无产阶级作家以后,这个名称就正式固定下来了。为了克服“拉普‘左派’的幼稚病”,不断深入探索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新方法,1934年第一次俄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俄国文学与俄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0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时不仅对苏联、欧美各国的文学产生过积极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坛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首先,在1933年9月《中央公论》上,德永直发表了一篇题为“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的文章。首先,他通过分析松田解子和贵司山治的两部作品,批判了藏原惟人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是“主观的、观念性的、艺术创方法上的毒虫”,是抽象的、机械的创作方法,并指出它几乎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家的金科玉律。他说:艺术应该由作家根据其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客观现实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尽管辩证法的世界观能帮助作家,但最基本的还是客观现实。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客观的真理,适用于所有的科学。用无产阶级的真理创作小说,这种命题本身就毫无意义。科学与艺术不同,艺术有其特殊性,无论政治、理论多么成熟,其本身都不能创造出艺术来。艺术是特殊的上部构造,这上部构造的特殊性就在于艺术的形象,艺术形象的形式就是艺术本质的形式,不能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文学的创作方法,主张消灭主观的、观念论的毒虫,驱逐机械论(103)。其次,他认为对当时苏维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什么的浪漫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上的口号,也不能突然拿过来使用。因为这些口号是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的口号,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大众生活的实际情况,而日本与苏联不同,存在着大众生活、客观现实的差异,因此,他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坚持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出发(104)。
德永直的这些观点很快就得到川口浩、久保荣的积极响应。1934年4月,川口在《文学评论》特辑上发表了“关于否定的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方向”一文,指出要清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过去的缺陷和谬误等,要重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方向。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含义,但它也并不是宽泛到毫无界限。其最根本的重要规定在于描写社会主义的真实。而社会主义的真实就是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的、所有工农群众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真实。只有当现实是社会主义的时候,作家才能讲述出社会主义的真实,苏维埃的现实是社会主义、真实的,其现实主义是积极的、肯定的。日本不同于苏联,现实是消极的、非真实的,否定的现实主义在当今才有意义(105)。翌年,久保荣也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指出日本和苏联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所面临的课题是,必须抱着坚信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阶级自觉,作为这统一战线中的先头部队来进行文学活动,而不是把苏维埃新锐的艺术理论占为己有。因为在统一战线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内部含有各种思想体系(例如: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等)和各种阶层,仅仅想用一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么一个口号去统一,这种机械的公式主义本身就践踏了有关“明确区别各阶层方法”的国际纲领。因此,他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无产阶级艺术运动向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艺术运动发展方向转换的时期,提倡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而绝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06)。
与上述论调相反的是森山启、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等人。他们都强调无产阶级作家应该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反映现实。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客观表现真实艺术的创作手法,所谓真实不仅仅只是单方面指社会主义的真实,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本身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艺术创作方法。此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以往的现实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再现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复杂的问题,指出产生矛盾对立的原因和解决的过程。
后来由于共产党受到残酷镇压,大批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者被逮捕入狱,关于这一理论引进的论争也就没有深入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德永直的论点虽然意识到文学的特殊性,但又错误地将世界观等同于文学的创作方法。在他看来,“为了从‘主题的积极性’、‘政治的首位性’等僵硬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呼吁大家要从无限丰富的现实中学习,即使没有世界观,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也是可能的。”(107)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性看法。应该说剔除世界观的创作方法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所持有的态度。文学创作根本离不开作家本人的世界观。因为任何一个艺术家都要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做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表明自己的倾向和态度。这种判断、评价和态度实际上都是由艺术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但艺术家并非哲学家,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事物的种种看法不会是以抽象的概念和论断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把艺术家等同于哲学家,把艺术作品等同于理论著作,把世界观等同于艺术的创作方法是极为荒谬的。艺术的审美取向离不开其特定的世界观。“艺术家在作品中对生活的看法和评价,以及他的整个创作活动,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一个世界观水平低下,充满庸俗、错误思想的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创造出伟大的作品。”(108)可见,世界观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进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没有充分进行下去,但它毕竟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以往的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方法如何摆脱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体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都有待于战后继承无产阶级衣钵的民主主义文学去思考、去解决。同时,它也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
总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是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以崭新的革命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学历史舞台的,无论在其理论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文艺主张不仅影响了一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者,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家和作家,而且还影响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爱好者。它为推动整个日本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为其后的日本文学开辟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它不愧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
————————————————————
(1) 平野谦:《昭和文学史》(筑摩丛书15),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26—27页。
(2)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反战主义者、进步作家、评论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作为人道主义者站在国际和平运动的前列,著有著名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1904—1912)、《欣悦的灵魂》(1922—1933)等。
(3)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43页。
(4)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00页。
(5)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00—301页。
(6)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44页。
(7) 所谓“私小说”是指作家将写作的重心放在个人切身的体验、或自己身边的人、或琐碎的事情上。作家注重心理描写,追求为艺术而艺术。在日本它又称作“纯文学”。
(8) 所谓“心境小说”是指“私小说”中的心境小说,作者采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反映个人日常生活琐碎的内容。像白桦派代表作家志贺直哉创作的《在城崎》便是典型的心境小说。
(9)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193页。
(10) 同上,第209—210页。
(11) 同上,第206页。
(12)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08页。
(13) 同上,第203—204页。
(14)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15页。
(15) 同上,第216页。
(16) 所谓“工联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年代初在西欧,尤其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盛行的激进工会主义。该工会主张排除一切政党活动,依靠大罢工、直接行动等来实现产业管理,完成社会改造。它又成为工团主义。把信奉工联主义的人叫做“工联主义者”。
(17) 所谓“工联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年代初在西欧,尤其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盛行的激进工会主义。该工会主张排除一切政党活动,依靠大罢工、直接行动等来实现产业管理,完成社会改造。它又成为工团主义。把信奉工联主义的人叫做“工联主义者”。
(18)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47页。
(19) “龟户事件”指1923年9月5日前后,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家平泽计七、川合义虎等10人在龟户警察署惨遭日本警察和军队的杀害。
(20) “大杉荣惨案”指1923年9月宪兵大尉甘粕正彦乘着关东大地震戒严令颁布时期的混乱,将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运动家大杉荣和他的妻子伊藤野枝及其外甥橘宗一带到宪兵队杀害了。该事件又称为“甘粕事件”。
(21)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48页。
(22)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21页。
(23) 同上,第222页。
(24) 同上,第224页。
(25) 平野谦、山本健吉等主编:《现代日本文学论争史》,东京:未来社,1956年版,第295页。
(26) 平野谦:《昭和文学史》(筑摩丛书15),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3页。
(27)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28) 平野谦:《昭和文学史》(筑摩丛书15),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5页。
(29)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49页。
(30)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05页。
(31)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32)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50页。(www.daowen.com)
(33) 同上,第253页。
(34) “农民文艺会”指大正13年(1925)成立的、以犬田卯为核心开展农民文学创作的农民文艺研究会。
(35) 所谓的“帝大”是“帝国大学”的简称,指旧制的日本国立综合大学。1886年根据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为帝国大学,1897年又设立了京都帝国大学,其后设置了东北、九州、北海道、京城、台北、大阪、名古屋帝国大学。
(36)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37) Nippona Artista Proleta Federacio在此为世界语。1906年,日本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语曾一度广为使用,到二战期间遭到排挤。
(38) 田山花袋(1871—1930),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棉被》(1907)、《一个士兵》(1907)、《乡村教师》(1909)等。他主张露骨大胆地描写一切,排除技巧,不要自己束缚自己的笔,提倡平面描写,不将个人的主观意识注入到作品中去,摹状客观事物、现象不深入其内部,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刻画亦然。
(39) 德田秋声(1871—1943),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典型作家。主要佳作有《足迹》(1910)、《霉》(1911)。他继承并实践了田山花袋所提出的文学创作主张,善于“平面直描”。
(40) 岛崎藤村(1872—1943),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杰出的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嫩叶集》(1896)、《落梅集》(1901)、《千曲川风情》(1900)、《破戒》(1906)、《春》(1908)、《家》(1911)、《新生》(1919)等。他主张文学的无解决主义,强调人物心理细微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
(41)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82页。
(42) 同上。
(43)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83页。
(44) 同上。
(45) 同上,第284页。
(46) 同上。
(47)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无产阶级文学》,东京:有精堂,1986年版,第157页。
(48) 转引自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48页。
(49)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47—248页。
(50)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86页。
(51) 同上,第290页。
(52) 同上,第292页。
(53) “我们”在此泛指无产阶级文学艺术。
(54) 同(50),第293页。
(55)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92页。
(56) 同上,第294页。
(57) 同上。
(58)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95页。
(59) 同上,第296页。
(60) 矶田光一、中村光夫等主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增补改订),东京:新潮社,1991年版,第936页。
(61)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14页。
(62)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15页。
(63)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20—321页。
(64) 同上,第327页。
(65)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东京:岩波新书,1999年版,第86页。
(66)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4》,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05—306页。
(67)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5》,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38页。
(68) 平野谦:《昭和文学史》(筑摩丛书15),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71页。
(69) 同(67),第345页。
(70)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230页。
(71) 所谓“四·一六事件”就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的逮捕日本共产党员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日本共产党中央指挥部一半成员被逮捕,受到了空前的打击。起诉者达339名。
(72) 所谓“主情”就是指“重抒情”,日本人在文学作品中喜欢抒发内心对自然的种种感受。咏叹自然是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
(73) 所谓“超政治性”简而言之就是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追求艺术至上主义的纯文学。
(74) “感物兴叹”是日本江户时期国学大师本居宣长(1730—1801)对平安朝的《源氏物语》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日语里写作“MONONOAWARE”。“感物兴叹”是日本古典美学理念,指“对所见之物、所听之事、所及对象产生情感的震动而发出内心的种种感叹”。它代表了日本古典文学最初的一种精神美,昭示着日本古代文学摆脱以往的中国汉文学模式,正式确立独具日本人审美情趣的、纯日本式的新文学模式的美学理念。
(75) “风雅”来自中国的《诗经》里的《国风》和《大雅》、《小雅》。但它完全抛弃了原汉语所赋予“风雅”的真意,被注入了符合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内容,即远离现实社会、政治,埋头于自然,顺从造化,和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它纯粹是一个日本式的概念。
(76)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1》,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50—351页。
(77) 同上,第355页。
(78) 同上,第356页。
(79) 在此主要是指进步的知识分子、农民或工人出身的文学创作者。
(80)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15页。
(81) 同上,第217页。
(82) 同上,第219页。
(83)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2》,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18页。
(84) 同上,第222页。
(85)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86) 同上,第38页。
(87)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77页。
(88) 同上。
(89)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78页。
(90) 同上,第280页。
(91) 同上,第282—283页。
(92)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83页。
(93)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4页。
(94) 同上,第735页。
(9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2页。
(96) 黄修已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97) 黄修已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98)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无产阶级文学》,东京:有精堂,1986年版,第166页。
(99)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页。
(100) 同上,第695页。
(101)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无产阶级文学》,东京:有精堂,1986年版,第168页。
(102)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103)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6》,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80—285页。
(104) 同上,第285—286页。
(105)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7》,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51—354页。
(106) 同上,第383—384页。
(107) 平野谦:《昭和文学史》(筑摩丛书15),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137页。
(108)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