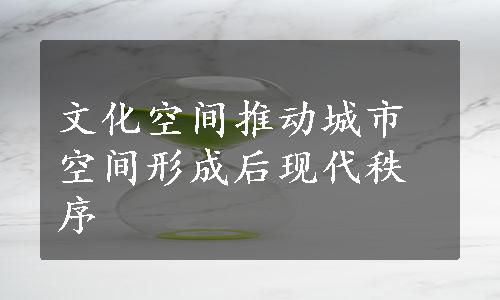
后工业城市,或者说后现代城市,试图摆脱工业生产唯一性的需求,追求生产与生活的平衡。生活世界的空间秩序“产生于空间的社会生产,各种人文地理的结构反映继而构建了世界的存在”(苏贾,2004:39)。文化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动力,巧妙地在城市词语中扮演了颠覆性的角色。文化空间所改变的城市空间,不仅是建筑风格的转换,更是一种以人的多样性和全面发展为底蕴的新秩序,是一种基于差异凝聚的后现代秩序。
尽管“后现代”一词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陆续出现于文化传播之中,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后现代”才正式登场。“后现代主义”最初用于指20世纪60年代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超越现代主义艺术的运动。随后,它被研究后现代艺术、后结构主义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拾掇起来。文学批评家们,如豪(Irving Howe)、费德勒(Leslie Fiedler)、哈桑(Ihab Hassan)和桑塔格(Susan Sontag),开始讨论文学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哀叹现代主义已经丧失社会批判的波西米亚式力量。建筑师,如文里图和詹克斯(Charles Jencks),开始关注当代建筑中出现的新形式和新现象,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怀着较为积极的情绪。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认为,这是对现代主义世界观的合理反抗:
一般被看成是实证主义的、技术中心论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现代主义,已经得到了相信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合理计划、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的确证。作为对比,后现代主义将特权赋予了异质和差异,它们是重新界定文化话语的解放力量。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2013:14-15)(www.daowen.com)
后现代主义快速进入各个学科的现象说明它具有强劲的渗透力,它将各个领域的注意力引向文化变迁(费瑟斯通,2009:61)。综合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宏观环境下,文化空间所推动的城市空间新秩序,具体表现为多种功能空间相互渗透、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以及现实性与虚拟性的交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