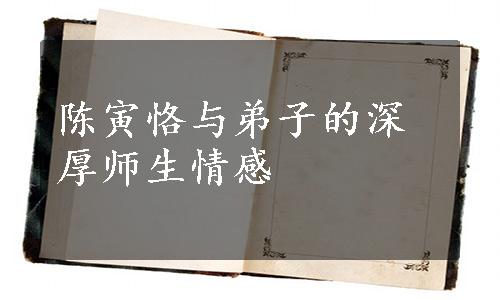
建国后,任职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被评为一级教授。1953年秋天,50岁的蒋天枢已逐步迈入了老境,到了含饴弄孙、优游林下的年龄,但他不顾路途遥远,专程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陈寅恪对这个弟子的远道而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欣喜。高兴之余,他特地写下了《广州赠别蒋秉南》两首七绝: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师母唐晓莹也吟诗赠蒋天枢: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
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要解读这两首七绝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需要多花点笔墨来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天地君亲师,人伦五大礼。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师所占的分量是很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尊师一直是天下读书人恪守的礼仪规范,已经完全融入读书人的精神血液,“程门立雪”作为尊师佳话经过文人墨客的咀嚼而代代相传。然而,世易时移,古礼不再。早在1951年,史学界的泰斗顾颉刚先生就以一篇《从我自己看胡适》,与自己的恩师划清了界限,顾门弟子群起而效尤,纷纷著文批判自己的老师顾颉刚先生,表达了与恩师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至于如何会出现这种师弟之间同室操戈、翻脸无情的怪现象,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曾做过一针见血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但这种违背传统伦理的行径无疑毒化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立雪旧时代的名师之门肯定不再是值得夸耀的好事,因为原来的名师多与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身家不清白”甚至“有尾惧诛”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原来的师门断绝往来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法门,名师门前冷落鞍马稀成为很自然的景观。作为旧史学的招牌,陈寅恪的目标很惹眼,不少陈门弟子也与他断绝往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独来南海吊残秋”正说明了陈寅恪当时内心世界的孤寂以及蒋天枢此行在陈寅恪心灵中所引起的震荡。(www.daowen.com)
确实,为人厚道的蒋天枢却是不以时俗为转移的士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颗“事师如事父”的传统文化情结。复旦校园里流传着蒋天枢不少趣事,甚至同一个故事有着不同的版本,其根本意思就是说明蒋先生是如何尊师的。而且为人厚道,性情温和,一派儒者之风形象的蒋天枢,偏偏在尊师重道上毫不让步,表现出种种的失态,以致人们私下说他“情绪偏激”,似乎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的风范,同行或学生谈起“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满贮崇敬之情,蒋天枢都会侧目而视之,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是不敬之举,何况直呼其名也。至于他自己,总是开口闭口是“静安先生”。有人以为他是王国维的弟子,蒋天枢满怀遗憾地说:“我没有赶上,只能算是他的私淑弟子。”许道明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记下了这么一件事,足以说明蒋天枢尊师之诚。同为复旦园“十大名教授”的朱东润先生,也是一代书生,喜欢说笑,言词无忌。所以在生活中,也时常表现出十分可爱的书生气。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有一次在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会上,朱先生讲治学之道,讲着讲着就讲到了陈寅恪。朱先生顺嘴评论说,寅恪先生学问虽然好,但晚年花了那么多精力,研究一个妓女,大可不必!还没等得在座老少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站出来,当着研究生诸位同学的面,指着朱先生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在平常的日子里,是难得有人给朱东润先生难堪的,这回给他的倒是十足的难堪。朱先生当场气得脸色发白,这则故事已成为复旦中文系的经典,代代相传,凡是进入中文系工作或者学习的师生几乎无人不知。这事传出后,成为赞叹陈门弟子尊师的佳话。
作为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目击者,蒋天枢可谓是陈寅恪最知心的门人,两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终其一生,师生之间从来没有产生感情上的芥蒂或龌龊,完全达到了心境的切合和沟通。陈寅恪经常把自己的著作赠给蒋天枢,蒋天枢也经常为恩师借阅各种古籍,两人来往不绝。1956年5月,陈寅恪在填写《干部经历表》时,把蒋天枢列入自己的“主要社会关系”:“1928年在清华是师生关系,最近数年因托他在上海图书馆查资料,故常有信来往。”这段记载使我们感知蒋天枢在陈寅恪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令后人为之感叹的是,1958年陈寅恪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批判靶子,经受政治火焰的炙烤时,蒋天枢依然毫不避讳同恩师的关系,在其《履历表》的“主要社会关系”栏目中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这是一种不需约定而自然生发出的心灵呼应,任何一位当事人在填写这类表格时,实际上借填表作为一种对彼此的思念的寄托,丝毫没有任何的矫情和做作。
蒋天枢对陈寅恪这种“事师如事父”的情怀始终如一,1964年蒋天枢先生南下广州金明馆探视困于床褥的老师,当时陈氏家中初陈寅恪外没有别人,陈寅恪目盲,没有给蒋天枢让座,年过花甲的白头老弟子如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地毕恭毕敬,站在同样是白头老师的病榻边面聆教诲,而且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程门立雪”,在蒋先生看来是学生应该躬行的本分。见落叶而知秋,从这些点点滴滴中可以窥知蒋天枢的内心世界。陆键东感叹“那是一种丝毫不需修饰的真情流露”。而蒋天枢终生引以为憾的是,当恩师仙逝时,由于书信的延搁,使他失去了前往羊城送别恩师的机会。
要进一步说明蒋天枢在陈寅恪心目中的分量,还需要探讨陈寅恪的交际圈。与“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胡适相比,陈寅恪为人冷峭,自负自许,他的名士心性和一身傲骨,使他不愿趋时,不求闻达,对政治更是凛然自警,不愿意过多涉入政治泥潭,以免亵渎了他视若生命并为之吟唱不休的“自由之学术,独立之人格”,继续秉承家父遗风,神州袖手,冷眼看世界,对于名利无所营求,寡交游,不为名士,不赶热客,人际交往圈子极为狭窄,能入他法眼的是满身洋溢着传统文化气韵的硕学通儒,是与陈寅恪在气类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彼此之间相知相挈心有灵犀。因此他的朋友圈子也有不同的层次,一般朋友仅限于书信往来,如陈垣、郑天挺、胡适、罗香林、袁同礼、王力等人;对比较密切的朋友,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陈氏夫妇常常用诗词酬答作为友朋交谊的珍贵礼物,借彼此之间的诗词酬答来吐露心声,寻求心灵上的共鸣。在陈寅恪的一生中,能够得到陈寅恪的赠诗的人为数极少,有傅斯年、刘弘度、杨树达、吴宓、冼玉清、向达等人,这些人都是与陈寅恪同时代、同一辈分的学人。再密切的知心朋友就属于高山流水的知音了,如王国维、吴宓、刘弘度等人。建国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陈寅恪的内心世界的大门关闭得更紧,他的交往圈子更加狭小,原来与他相交颇厚的一些人因为各种变故而与他疏远,他的人际交往圈子发生了分化,如以前与他交情深厚的陈垣以后断绝往来。至于他的弟子门人中,能够得到他的赠诗的就更是凤毛麟角,蒋天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由此可见,蒋天枢深得陈寅恪的喜爱与信赖。深刻了解陈寅恪内心感情世界的蒋天枢完全能够掂得出恩师赠诗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分量。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著作的流传后世是文人一向关注的最大的身后事。所谓“所南心史井中全”指的是南宋学者郑所南为了保存自己的著作《铁函心史》,陈寅恪赠弟子蒋天枢诗有“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在《別传》的緣起,又說“珍重承天井中水”,“承天井中水”是隱喻郑所南的《铁函心史》。《心史》記述南宋亡國后遗民之痛,在井中密藏三百多年后才重见天日。陈寅恪將自身对民族文化存亡有感的“心史”藏在《柳如是別传》中,希望后人珍视秘藏在重重詩文典故中的的隱语心事。郑思肖,字所南,生在宋亡元兴之际。陈之藩《失根的兰花》文中說,郑思肖画兰,连根帶叶都浮在空中,是伤心“国土沦亡,根著何处?”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他用铁函把它密封起来,然后把铁函藏在苏州承天寺的井中,一直到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苏州承天寺僧人在古井中,掘得一物,清洗后見是一铁函。在打开锡匣、蜡漆、包紙的层层密封后,赫然发现题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的文稿,后世称之《铁函心史》。从古井保存到重见天日,历经两个朝代300多年。
在这里陈寅恪提到这个典故,并非仅仅用来说明民族文化有赖于文化托命之人的艰辛保全,而是有沉重的心事传递给自己的爱徒,有着古典难以包容的“今典”。已进入桑榆晚景的陈寅恪最念兹在兹的是他的著作整理和保存问题,“文章存佚关兴废”,陈寅恪纵横学术绝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其学术活动总是与时代风云暗相呼应,对学术文化匡正社会风俗、有俾于治道一贯充满自信,“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朱延丰突厥统考序》)如果门下弟子如云,就象孔夫子那样,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检书代笔有门人”,自然有弟子代为整理其著述,并把老师的学问发扬光大。然而昔日桃李满天下的陈寅恪已是晚景寂寥,门前荒凉,学术承继乏人,联想到此,陈寅恪伤今怀古乃至潸然泪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蒋天枢的出现使陈寅恪看到了托付整理学术名山的最佳人选,陈寅恪才敞开心扉,向他的弟子吐露心事,也就是第二首七绝中所表达的内容。正如陆键东先生所言:“若以与陈寅恪接触的渊源而言,比蒋天枢更深的陈门弟子大有人在;若以治史才华而言,比蒋天枢更深刻地理解陈寅恪学术精髓的陈门弟子也不在少数,但陈寅恪只认定蒋天枢。”蒋天枢能入其师的法眼,固然与蒋天枢的品性深得恩师嘉许有关。但50年代的陈寅恪环视身边左右,已找不到为陈寅恪可信赖的弟子,难以找到可以托付身后事,也不无关系。这是史学大师的不幸,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不幸。
“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向是传统学人奉为圭臬的交往准则。陈寅恪与蒋天枢之间的交往也是天然去雕饰的人间至真至性的君子之交。蒋天枢除了经常给恩师学术研究转借各种版本,提供大批研究资料外,似乎很难见到扣人心弦的场面。但蒋天枢手中却保存了一件陈寅恪夫妇赠与的珍贵纪念品。这件纪念品为我们了解陈寅恪和蒋天枢的感情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那还是1957年五月间,康乐园东北区竹类标本园有一丛竹子上结有形如雪梨的竹果,累累竹果甚至把竹子都压弯了,这一大自然的奇观引起了中山大学师生的注意,连《中山大学周报》都进行了报道。陈寅恪夫妇听说后,也前来用心灵感受大自然的奇观,得知这种竹子是“印度象鼻竹”。于是唐晓莹就画了一幅“印度象鼻竹”图,陈寅恪赋诗纪念,即《丁酉首夏校园印度象鼻竹结实大如梨晓莹学写其状寅恪戏题二绝》:“西天不恨移根远,南国微怜结实迟。多少柔条摇落后,平安报与故人知。青葱能保岁寒姿,画里连昌忆旧枝。留得春风应有意,莫教绿鬓负年时。”王谢之家,不废文事,陈氏夫妇一直保持着旧时贵族家庭的闲情逸致和一贯做派,诗词唱和,琴瑟相应,这样的风韵雅事在陈氏夫妇的生活场景中经常出现,是夫妇感情生活伉俪情深的真实流露,一般秘不示人。但陈氏夫妇仍把他们两人诗画合璧的印度象鼻竹图赠给蒋天枢,反映了陈氏夫妇对蒋天枢的信赖。“闻弦歌而知雅意”,蒋天枢对恩师的深情厚意感铭肺腑,多年不能忘怀。陈氏夫妇弃世多年后,蒋天枢仍在其《楚辞论文集》中忆及此事:“昔年陈师有咏《印度象鼻竹实》诗,师母绘竹实图并书诗其上以寄枢,‘莫教绿鬓负年时’。所以勖枢也。……今兹衰老,追怀往事,感恨曷及!”蒋天枢向来不是挟师名而自重的人,在陈寅恪文名满天下的时候,蒋天枢从不打着其师的旗号而炫耀自己;在陈寅恪谤名满天下的时候,蒋天枢也同样执弟子之礼,倾情呵护师生之间的脉脉温情,用高洁的人格和精湛的学术来报答老师的培养,用共通的心灵世界来相互支撑悲苍的人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