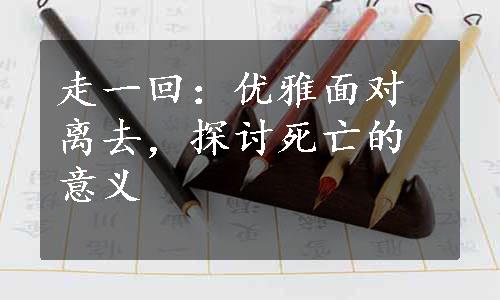
用文字潇洒走一回
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父亲突然辞世,我平生第一次去参加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殡仪馆里转了一圈,找到好友,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他,也许我无声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当我看到很多人走近灵堂鞠躬志哀,而逝去的人则毫无反应地静静躺着,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寒意,那种冰凉的感觉让我在刹那间对生命的热乎乎的温度的体验更加深刻。我在想,那种因为灵魂和思考而产生的热,该借由什么传下去呢?
不妨再举个例子,村里的一个老婆婆去世了,他们在办丧事的时候儿孙满堂哭着喊着,请来的鼓乐队也在热闹地吹着打着。当然,哭闹吵嚷都无可非议,这是很典型的死亡场景。但我忍不住很有感慨地想,有的人死了,就真的死了。他日,我该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告别自己的生命呢?我又该以怎样的一种优雅又充满自主的方式让生命延续呢?
克洛德西蒙在《弗兰德公路》中的一句题记:“人们以为是在学习生活,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也许当我也僵冷平直地合上眼睛的时候,我才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什么都是一场空的道理,我会多么希望能有些东西作为“提示物”(Reminder),陪伴我挚爱的亲人和朋友,继续接替我表达一些诸如“意义”的思索。那时候,我想到的是诸如一本书,一首歌,或是一些艺术品之类的媒介。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生命只能徒劳地挣扎,因此,每个人都想延续自己的生命,比如生儿育女、比如敛财聚宝、比如沽名钓誉等等,我也一样地曾想过那样去延续,但后来发现那种方式的延伸根本不适合我,我就是要做那种借由文字的灵性仍然活着的人。
我们生活过的大千世界以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使曾经如花盛开过,如云绽放过,如光璀璨过,如霞绚丽过,如风如影,如诗如梦,如同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美好的喻体。一切都会过去,好的坏的,统统都会过去,不管你的金钱、权力有多大,位置、头衔有多显赫,人死了一切也都随风而去。那种靠权位、金钱换来的尊重其实是虚假的,都会随着它们的褪去去烟消云散,但有的人却赢得了长久的怀念和尊敬。他们死了,仍然活着(这和鬼神之类的故事并没有关系),他们借由他们所创造的文学、音乐或艺术把灵魂留了下来,后人在他们的作品的喜怒哀乐里沉浮。正因为如此,我们遗忘了多少皇帝将相达官贵人,但却把一些才子佳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文字烙印在心里。
正如《黄河谣》唱的那样:“就是这么走的,就是这么过的。”作为共同的结局,我们没有理由不关心这一回该怎么潇洒地走过。我们必须承认,自然意义上的生命都如同一阵风,吹过了就真的消失得了无影踪,而那些真正能借由我们的缅怀而存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能够表达我们灵魂鲜活时的东西,通过那些作品,死者才可以仍然有灵性地活着。这也是写作的意义所在,哪怕是一个私密的不为发表而作的文本。也许多年之后,在我死后,你依然可以看着我写下的文字,你对我文字的阅读其实就是在与我对话,你的情绪在我的文字中波动,如同我的情绪也曾经波动一样,只不过我也许替你说了你没有说出的话,或许你也曾替我说出了我没有说出的话,我们的灵魂在这些文字中共舞,你继续写更多的感想传了下去,我也因此而获得了延续。只有这样,我们试图被延续下去的愿望才变成可能,才有了点永恒的意义。(www.daowen.com)
偶然翻开少年时代的日记,许多早已淡陌的往事一下子被拉到了眼前,那些青春鲜活的人与事突然间被激活。日记的文字,就是一种重生的手段,没有了它们,那些年少的心情可能真的就“被雨打风吹去”了。因此,要潇洒就得如司汤达那样:活过、爱过、写过、唱过、被共鸣过,这一切才足够。至于潇洒走了一回之后的事,就是如何面对“离去”,因此,我们对死亡的探讨不妨可以再宽容点,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似乎就是如何优雅地走,我们总是觉得世事匆忙,很少有人能冷静地坐下来想自己的后事,因此大部分的人都是带着遗憾走的。除了自杀之外,能够有准备地去世,不带着遗憾地走应该是一种很理想的方式,而最好的为生命的告别而做的准备(或定格)就是著书立说。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自己的离去的最理想的方式,我想我若能留下我的灵魂来过的证据和灵性歌唱过的证据就很知足了。文字也好,声音也好,它们都是有感情的。人死了,如果作品能够触动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默契,引发后来者的共鸣,这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种永恒。
当然,在文字里袒露自己,这是需要勇气的,这也是很多写了不少东西的人死之前仍然要交代销毁掉他们的作品的原因。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许多明哲保身随时准备说笑嘲讽跟喝倒彩的旁观者,但整个社会文明需要那些勇敢一些的人来延续和推动,尽管和沉默的大多数相比,勇敢的人成了少数,成了“弱势”的一小撮,但正是这少少的一小撮,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激情,让我们反抗了平庸。用生命去书写的人,其实是最无私的人。他们记录下的灵魂的悸动和震颤,启发了他人,启迪了后世。正如农村中过着艰辛生活的汉子,偶尔会主动喝醉了,胡言乱语一通,给家中老小左邻右舍带来一点小小的骚动刺激和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柄,作者的一丁点小痛苦就是农村汉子口中难以咽下的苦酒,但却意义非凡。
一个写作的人应该相信,在他(她)找到的知音里,哪怕只有一个后来者能从中受益,其意义就足以压倒所有的耻笑。有人经常拿张爱玲的晚年和去世来说事,觉得那样孤苦伶仃连死都不为人知很不值得,但我想这也许是对死亡的认识上的差异,其实她是“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早在1937年她就借《霸王别姬》的女主角表达过自己的态度了。在中国文化关于死亡的观念熏陶下,许许多多老人毫无意义地热闹地死去,但张爱玲却只有一个。
三十来岁,我就早早地揣测了生与死的意义,并让自己的生命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感觉潇洒地往前行进,我的生活也逐渐从晦涩走向澄明,从被动走向自觉,这样的认识突破似乎有点不容易,但对我而言似乎是水到渠成,我想不管日子再怎么凄凉孤寂,我都会认真地过每一天,从青春犹在的英年,到淡定安祥的晚年。此外,我希望能够在告别世界的时候,把所有有用的健康的器官都摘除,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从而让自己的肉体也能以另一种独到的方式延续,不妨想象一下,眼角膜可以帮助另一个重获光明,心脏可以继续跳动在另一个躯体,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即便剩下的肌体残余一无是处,也还是可以作为有机物肥料,不妨找一块贫瘠的土地,把它们深深地埋进去,再在上面种一棵树,春天来的时候,我依然能以某种形式让自己沐浴在春光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