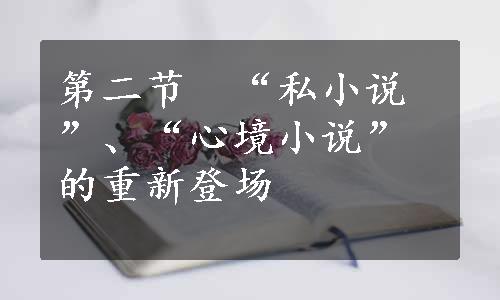
“私小说”和“心境小说”都是日本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独具日本特色的小说创作形式。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平安朝时期(794—1192)的女性日记文学。只不过,到了近代“私小说”才以正式的形式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自然主义文艺思潮风靡日本时期。当时由于国情的差异,再加之明治政府推行的不是一条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路线,人们的言行、集会等常受到封建式政府独裁统治的压抑,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们就无法像西方自然主义作家那样通过观察,真实地描写出现实社会中人和事的真面目,只好把焦点对在了自己身边的琐碎事情,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个人问题的关注,把对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独白,把文学创作的素材锁定在“自我”的领域中。因此,“私小说”成了欧洲资本主义文学在日本的“变种”。
到了大正时期,日本著名评论家久米正雄等人又主张把着力于表现作者个人心境变化、吐露个人强烈内心感受的一类“私小说”称为“心境小说”。这样,关于“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就成了文坛论述的核心。到了战后,评论家们像伊藤整、平野谦等人又根据作家的文学创作态度,对“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又再一次重新诠释,把“私小说”分为“破灭型”和“调和型”这两种形式。可以说“破灭型”是指文学创作者不敢正视现实与人生,不愿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和复杂的人生,往往会产生一种逃避、绝望、厌恶、放弃的消极态度,而“调和型”是指文学家面对现实生活和人生中的不安与矛盾,能采取善意、乐观、和解、调和的积极态度。前一种被视为狭义的“私小说”,而后一种被称为广义的“心境小说”。这两种小说的创作形式在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以前一直占据日本文坛核心地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起到了催生作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始在日本渐次蓬勃发展。同时,欧洲的先锋运动也开始波及日本。以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艺术派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对垒。这样,在“革命的文学”和“文学的革命”占据文坛时期,“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创作走向了低迷。
一、“私小说”、“心境小说”的重新登场
据评论家小田切秀雄考证:“私小说”这一名称是久米正雄和中村武罗夫在19世纪20年代《新潮》杂志举办的座谈会上最先使用的。
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日本的报纸、杂志到处散见着一些关于“我就是小说”、“所谓私小说”、“‘自我’小说”等用语。针对这种现象,中村武罗夫(1886—1949)写了一篇题为“严肃小说和心境小说”(1924)的文章,生田长江写了一篇名叫“偏重日常生活的不好倾向”(1924)的文章等,批判“私小说”只不过是“叙述作者心境的小说”(4),“不是小说创作的正道”(5)。对此,久米正雄却抱以不同的见解。他在《私小说和心境小说》(1924)中这样阐述道:“心境小说主要表达人生观的感想”,主张“私小说是小说的根本‘正道’,故事情节是第二位的”(6)。由此,“心境小说”作为“私小说”的一种类型而正式得名。“私小说”作为文学观念上的问题正式被认同,并且加以理念化。龟井胜一郎(1907—1966)在谈到“私小说”时说:“私小说是日本的传统文学,是直白地描写作家的内心和身边琐事的小说。”(7)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小说”在日本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时起,至今,“私小说”仍是日本纯文学创作的主体。战后,“私小说、心境小说是日本小说不容回避的传统。老一代文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以纤细敏锐的感性不懈地追求微观世界。”(8)由于受到社会变革的冲击和现实社会运动的影响,“私小说”的作家们也试图打破旧的传统,在创作手法上虽然保持了以往“私小说”的表现形式,但在内容上多少有一点变革,个别作家开始把笔触从个人生活映射到社会生活,通过个人的生活经历抒发对社会和时代的看法,此时的“私小说”包含了一定社会内容,像《灰色的月亮》、《战争者的悲哀》、《遥拜队长》、《狐》等都是反映战争时期遭受心灵创伤的个体分子的作品。
如果说战后初始老一代著名作家和成名作家复活的一系列作品,是战后文学复兴的开篇之作,那么,“私小说”、“心境小说”的重登文坛就是战后文学复兴的第二浪潮。像上林晓、尾崎一雄、檀一雄等传统文学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中坚作家们纷纷登场,一如既往地避开战后的现实生活,把自己封闭在周围的狭小天地里,细细地玩味种种体验。其主要的作家和作品有:岛木健作的《赤蛙》(1946)、尾崎一雄的《虫子的二三事》(1948)、网野菊的《金棺》(1947)、上林晓的《在圣约翰医院》(1946)、平林泰子的《这样的女人》(1946)、檀一雄的《律子之爱·律子之死》(1948)、田宫虎彦的《画册》(1950)和《菊坂》(1951)等。其中,《虫子的二三事》颇具典型意义。尾崎一雄在小说里描写了“我”卧病在床,根据自己的细心观察、玩味蜘蛛并由此而联想到跳蚤、蜜蜂、苍蝇等各种小虫子的不同习性,描写它们都为自己的生存而不断努力的故事,借此来表现作者本人在病中对人的生与死的思索和体验。
从总体上来看,上述这些小说大都是作者通过自身的病痛、或者是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如妻子、孩子等人的疾病、爱恋或者死亡,来体味战后生活中的各种危机,特别是生死问题。这种日本传统式的情绪释放和东方虚无主义的直觉会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在文艺理论方面,伊藤整首先在文章“小说的方法”(1948)中强调真正的小说就是“私小说”,它主要是一种作者描述日常琐细事情的语言艺术。其次,他在“调和与放弃”(1948)的文章中提出了“调和”和“放弃”两种“私小说”的表现方法,即调和、把握现世和放弃、破坏现世。接着,他又在“小说的认识”(1950)中指出要将两者统一起来的认识论。平野谦在其论著《艺术和生活》(1958)里论述“私小说”时,对“私小说的二律背反”问题进行了阐明,同时还对“私小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
如果将生的危机意识当作唯一创作的主题,并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这种危机感的话,就会逐渐产生在现实生活本身设定危机的倾向,最终达到破坏生的地步。如果在警惕、克服这种生的危机里招致现实生活上的调和,自发的创作热情就会渐渐呆滞,不得不愈发沉抑。总之,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创作理念保证我国独特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是不得不越发暴露围绕现实生活和艺术相关联的二律背反矛盾。(9)
他还举出了大量的例证,说明“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相互包含的二律背反都是源于它同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他又指出作为优秀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都应该以拯救现实生活上的危机意识为创作主题。他认为“私小说”和“心境小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即“私小说”是破灭的文学,“心境小说”是拯救的文学。前者在于表白无法克服现实社会中混沌的危机,后者的结论是能克服这些危机;前者是源于外界和自我的不协调,后者则是努力探求它们之间存在的和谐点;前者代表了无理想、无解决的自然主义文学,后者代表了理想主义的“白桦派”文学(10)。由此,“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分化为“破灭型”私小说和“调和型”私小说。
总之,无论哪种类型的“私小说”,都是以孤寂的自我独白为重心,缺乏广泛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整个战后的现实生活,作家们把自我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专心致志地仔细体味自我生活,从而无法充分地、立体地反映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体,无法抚慰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幸存者的内心创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作品不太具有现实社会性,这是“私小说”特别是战后“私小说”的一个局限。
其实,早在战前日本文坛就曾对“私小说”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主要源自小林秀雄在《经济往来》杂志5—8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私小说论”(1935)的文章,提出了“私小说”执著于自我独白的、缺乏社会性的性质,提出了经过社会化的自我的问题(11)。他指出法国自然主义的文学家们所展现的“私小说”中的“自我”是已经被社会化了的,而日本的“私小说”却缺少社会化了的“自我”(12)。小林提出的“社会化了的‘自我’”理念最终经过战后20年,被“第三新人”所接受,将社会化的自我固定在家庭小说的创作上。战时,由于纯文学受到日本法西斯当局的钳制,横光利一在“纯粹小说论”中,提倡“小说俗化论”,试图否定“私小说”,变纯文学为通俗小说。战后,中村光夫(1911—1988)也针对“私小说”局限于自我的表现、过于强调写实而缺乏社会性视角的缺陷,写了论著《风俗小说论——批判近代写实主义》(1950)。这里的“写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指“自然主义”。中村通过论述近代自然主义的发生、发展、变质和崩溃的过程,批评了自然主义日本化的“私小说”盲目、错误采用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手法,从而丧失了文学的想象力,只描写自我的生活实感,缺乏社会性的倾向。其具体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村翔实地论述了自然主义产生、展开、变质和崩溃的过程,从整体发展趋势上深入分析了“私小说”虽然在技术上成功地将自然主义日本化,但是由于曲解而带来了负面影响,即在文学理论上片面而武断地误解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从而只注重实证手法,强调写实,缺乏虚构与想象,只是客观而忠实地描写自己有把握的所想所感,其作品缺乏社会性。
第二,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缺乏社会性的原因源于作家们这样一个文学创作理念,即认为文学直达内在的世界是最为重要的。中村认为要构建新的文学,就要恢复“私小说”已经失去的虚构性和社会性这两个要素。
第三,中村对战后重返文坛的一批风俗小说家如田村泰次郎、石坂洋次郎、舟桥圣一、丹羽文雄、林芙美子等所写的一些流行“风俗小说”,如田村泰次郎的《肉体的恶魔》(1946)和《肉体之门》(1947)、石坂洋次郎的《石中先生品行记》(1947)、舟桥圣一的《雪夫人画卷》(1948)、丹羽文雄的《让人讨厌的年龄》(1949)、林芙美子的《晚菊》(1949)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小说明显地缺乏社会性和思想性,只重点描写了战后混乱而颓废的世态人情。此外,他还明确指出,近代日本文坛在移植西欧的现实主义时,摒弃了其思想性,只单纯吸收了其创作技巧或者感觉的部分,从而导致“私小说”文学创作向通俗小说的方向倾斜。他在批判风俗小说的无思想性和在风俗小说领域中文学精神的贫弱时,形容战后的风俗小说是“在战时的阴郁的逼迫下受胎,作为战后混乱中的私生子成长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小说是从‘现代日本文学’的‘扭曲’中产生的必然结果”(13)。
综上所述,无论是“私小说”、“心境小说”还是“风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后饱受文化荒原之苦的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这些小说毕竟表现了日本人纤细的直觉性和敏感性,作家们将创作的重心放在了自我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上。他们以追求细腻、真切、富于感性的表现手法,传达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微妙的心理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式小说创作的内涵。但也要认识到在当时它们最大的一个局限就是缺乏社会化的自我(小林秀雄语),没有把文学创作的主题完全扩展到对整个现实社会的思考,没有对战后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的挖掘,没有随着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战后文学的革新而产生实质性的新变化,更无法给战后彷徨的人们带来心灵慰藉。
二、“第三新人”的登场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两国之间的“对立”进入冷战时期。50年代以后,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冷战也愈演愈烈,美国也开始改变了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把统治的权力移交给日本政府,原先它所推行的民主改革的势头逐渐减退。1951年日美双方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后,美国愈加想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一个重要战略地区。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一方面,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日本完全成了美国后方最大的军需供养基地。军需产业的急速增长刺激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庇护下,国内群众性的民主革命运动受到遏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追求享乐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战后派文学似乎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走向解体,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也陷入低潮。此时,由竹内好、伊藤整等人提出了“国民文学论”(1952),就此引发了日本文坛的一场论争。结果,“风俗小说”、“私小说”等再次流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异于“第一战后派”、“第二战后派”文学创作理念的“第三新人”作家群开始登上日本文坛。他们是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小岛信夫、庄野润三、三浦朱门、岛尾敏雄、远藤周作、阿川弘之、小沼丹(1918—1996)、武田繁太郎(1919—1986)、井上光晴以及女性作家曾野绫子等。作为评论家有远藤周作、服部达(1922—1956)、奥野健男(1926— )、村松刚(1929— )、日野启三(1929—2002)、进藤纯孝(1922— )、武井昭夫(1927— )、吉本隆明等。
“第三新人”的称呼最早见于山本健吉(1907—1988)在1953年1月号的《文学界》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第三新人”的评论文章。从此以后,媒体记者和一些评论家像服部达、奥野健男等人也多次使用这一用语,最终把它作为正式的文坛用语固定了下来。
1953年上半年到1955年上半年是“第三新人”文学创作的高潮。这期间,他们几乎包揽了一年两度文坛所颁发的日本纯文学最高奖项——“芥川文学奖”(14)。1953年春季第一个荣获29届该文学奖的是安冈章太郎。他以《凄凉的欢乐》(1953)和《坏伙伴》(1953)两部力作掀开了“第三新人”文学的新篇章。紧接着,于翌年的上半年,吉行淳之介以《骤雨》(1954)荣获了第31届“芥川文学奖”,下半年小岛信夫以《美国人学校》(1954)、庄野润三以《游泳池畔的小景》(1954)获得了第32届“芥川文学奖”,到了第三年春季远藤周作以《白人》获第33届“芥川文学奖”。其中,也不乏荣获候补提名奖的“第三新人”作家,如三浦朱门以《斧头和马丁》(1953)、曾野绫子以《远方的来客》(1953)获1954年春季提名奖。他们的登场,为“第三新人”的文学方向定下了基调,从此备受文学界的瞩目。
由于“第三新人”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度过了青春期,战前他们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战争中几乎没有亲赴战场、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炮灰的经历,当日本战败时又正值20多岁,尽管社会政治格局发生着激烈变化,但到了50年代日本经济在短短的时间内逐渐摆脱了战时和战败初期的困境,开始由倒退走向发展,人们相对迎来了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太平”、“安定”时期,再加之社会民主革命浪潮走向衰退,所以他们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比“战后派”文学家们弱得多。他们并不关心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对国家政治也抱以冷漠的态度,更谈不上表现文学的批判精神。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主题重心自然由社会重大问题移向自己身边的日常琐碎生活。他们把文学创作的审美取向放在了传统文学“私小说”的狭小天地。这样就导致“第三新人”的文学与“战后派”文学背道而驰。就连吉行淳之介本人在“我的文学放荡”(1965)一文中也承认,自己与“战后派”有距离,自己的作品是想通过描写“我”这个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来突出一个抽象主题的;安冈章太郎则说,他们要营造“小小角落里的另一个世界,即在自己的精神形成过程中,在自己的内部营造一个从自己的周围所得不到的另一个世界,并蛰居其中。”(15)显然,他们是继承了战前传统“私小说”的创作手法。
通过“第三新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他们善于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出发,在取材范围上立足于身边的种种日常生活,在艺术手法上倾向于传统“私小说”的自我追求,重视细节描写,文笔真实、细腻,叙述了许多普通市民阶层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感情纠葛、苦恼、不安与家庭破碎等现象。特别是市民家庭的瓦解、家庭成员之间的悲欢离合成了文学素材的主要取向,像安冈章太郎的《家庭》(1954)、《海边的光景》(1959)、《合家团圆图》(1961)、《夜幕降临之后》(1967),小岛信夫的《马》(1953)、《拥抱家族》(1965),庄野润三的《游泳池畔的小景》、《静物》(1960)、《浮出的灯塔》(1961)、《路》(1962)、《傍晚的云霞》(1965),曾野绫子的《远方的来客》,岛尾敏雄的《死亡的荆棘》(1960),阿川弘之的《夜晚的波涛声》(1967),三浦朱门的《偕老同穴》(1963)、《庭院盆景》(1967)等都是此类作品。在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家庭结构、人员亲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那些平时看似平静、和睦的家庭内部实际上却隐藏着种种危机和异常。作家们正是通过个人敏锐的感受性才捕捉到了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另外,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勾画的人物大多为厌恶学习、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劣等生,生活失意的弱者,带有屈辱感或生理缺陷的自卑者,前途无望的灰心者,性变态者,一生坎坷不平的小人物等。首先,就安冈章太郎的作品来说,《坏伙伴》中的“我”就是一个厌恶上学、没有生活目标、丧失理想的人。当“我”接触了坏朋友藤井高丽彦之后,一下子沾上了很多恶习,并以此为荣耀,带坏了其他原本单纯的劣等生苍田真悟。坏伙伴们整日徘徊在东京街头,无法抗拒太平洋战争前夕来自日本社会的沉闷压力,对前途不抱有任何希望,一味沮丧度日,浪费青春。《当铺的老板娘》(1960)中的“我”在社会上似乎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当“我”和妓女出身的老板娘坠入情网时,两人的感情却不被周围人所看好,一再遭到他人的白眼,精神世界几乎崩溃。其次,再看一下小岛信夫的作品。他的《口吃学校》(1953)和《微笑》(1954)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的弱者,同时又都是具有生理缺陷的自卑者。一个是患有先天性口吃,在学校里备受他人的歧视,对学校生活产生恐惧感,出现厌学心理,另一个是患有先天小儿麻痹症,内心始终充满了一种哀伤和自卑,而作为病患的父亲内心却交织着一种爱与恨的混杂情感。《美国人的学校》中的伊佐是一个性格内向、懦弱的英语老师,在美军占领时期,当他和一批英语教师参观美国人的学校时,却害怕讲英语。看到其他日本人能流利地说一口英语时,自己却产生了一种躁动和不安,一方面不愿意使用敌方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为此抱有自卑感。再者,吉行淳之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代表了社会的下层妓女。像《贩卖蔷薇者》(1950)、《原色的街道》(1951)、《骤雨》、《娼妇的房间》(1958)、《床之舟》(1958)、《沙上的植物群》(1963)等一系列作品都是以花街柳巷的风俗人情为题材,描写了恋情以外的男欢女爱、性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男女肉体与精神间的隔阂、感情寄托与生理需求之间的失衡等。性关系已不再单纯是家庭关系中夫妇间的情感交融,它已经走进了风俗业的烟花巷、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复兴所带来的不良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第三新人”的文学注重传统“私小说”的回归,看重眼前的日常生活,忠实于自我感受,尊崇文学的艺术性,追求艺术至上主义。他们把创作的内容集中在对人世间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般影像、特别是对下层弱势群体的面影的描绘上。作品充满了一种自虐自嘲的口吻,笔下的主人公总是以一种恐惧不安、躁动忧郁的眼神洞察社会、家庭潜在的危机,面对外界的压力、生活的窘境无力释放与解脱,只是被动地接受,灰心沮丧。他们的文学给人产生的第一印象就如服部达在1955年发表的论文(16)标题所言:“劣等生”、“小残废者”、“市民”。这也许同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因为这个流派的大多数作家都出身于下层社会,或从小就厌恶上学,或高考落第,或有生理缺陷,或因病没有完成学业等,他们进的学校也大多为二流或三流,与他人相比具有很强的自卑感,对周围的环境、眼前的事物十分敏感。日本现代著名评论家江藤淳(1933—1999)在“成熟与丧失”(1967)一文中评论“第三新人”时,特意将他们同“第一战后派”作了一个比较,认为前者是一些行为不端的旧制中学生,后者是一些“左派”大学生(17)。因此,他们笔下的文学形象多为逃学的劣等生、受气的下等士兵、残废者和多余的人。对此,服部达对“第三新人”下的评语是:同样属于30岁的这一代人,优等生(指阿川弘之、堀田善卫等人)已经很快成了作家,而剩下的一批人只好采取反击的办法,即不相信外部的世界,不相信高远且绝对的思想,承认自己不是优等生,承认自己平凡而卑微,而且不会像大多数“私小说”作家那样摆出一副严肃、沉思的神情。这种思维方式成了“第三新人”的模式(1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三新人”的文学在当时应该属于弱者的文学。
关于第三新人的特征,服部达早在“新时代的作家们”一文中(1954)就明确地概括为以下六点:
1.Bieder-meier-still式的格调占优;
2.和“战后派”作家相对立;
3.依靠朴素、实在的真实感;
4.接近“私小说”的传统;
5.批评性较弱;
6.欠缺对政治的关心。(19)
服部达指出,第一点所谓“Bieder-meier-still式的格调”一词流行于19世纪的德国,其风格是以简洁、实用和无趣味为主要特色。用在“第三新人”的文学特点上,主要是指他们的作品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简洁”、“条理性”和“小市民性”的倾向。第二点主要是指“第三新人”作家的文学特征具有“实事求是性、日常性、生活性、维持现状性、传统性、抒情性、单纯性、单调性、私小说性、形式性、非伦理性、非逻辑性、反批评性、非政治性”(20)的特点,这和“战后派”文学的很多特点都是相悖的。如果把“战后派”文学称为“硬派文学”的话,那么“第三新人”的文学就该叫做“软派文学”了。且不管他们文学表现的“非伦理性、非逻辑性”等,也可以说抓住了很多特色。第三点是指“第三新人”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会抱着一种“怀疑”的眼光或“有意识地拒绝非具象性、抽象的乃至唯心的实在感”。他们喜欢把作品的世界放在“日常生活的延长”上加以展开。第四点是指就“第三新人”在文学创作的手法而言,他们坚持“素朴、实在”的描写方式,以自叙形式如实描写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努力向传统的“私小说”回归。第五点是从“第三新人”所创作的文学效用来说,它表现的不是复音的而是单音的,不是和声的而是旋律的,不是戏剧性的而是抒情性的,具有形式性和便利性,不是试验性而是维持现状性。不过就吉行淳之介和安冈章太郎来说,他们的文学已经超越了这些框架。第六点认为“第三新人”受传统文学的影响很大,在表现文学主题时“缺乏对政治的关心”,这是由他们的“非伦理性”和“非逻辑性”带来的(21)。应该补充的是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导致了他们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缺乏深度认识。这一切都促使他们不关心政治。(www.daowen.com)
此外,日本现代著名评论家松原新一(1940— )在《昭和文学》(1972)中撰写了一篇题为“现代文学的动向”的文章,当他论及“第三新人”的特点时,提出的观点是“对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表示厌恶、反感”、“观念性和思辨性匮乏”、“对自己的资质、纤细的感受性的能力、真实感受报以忠实的态度”、“比起作品中的问题性的大小,更注重其艺术性的浓郁”、具有“私小说式的手法和格调”(22)等等。总体来看,应该同服部达的观点如出一辙。
应该指出的是,“第三新人”只是在同一段时期登上日本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根本就没有一个系统的、一致性的文学理念做引导,仅仅是在创作方向和风格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正因为他们在文学表现上彼此都十分重视自身强烈而又率直的感受性,所以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就必然使作家们在创作文学作品中产生同中有异。一些独具个性魅力的作家及其作品不乏存在,像阿川弘之虽然没有获得“芥川文学奖”,但作为“第三新人”,他继承了大正时代素有“短篇小说之神”之称的志贺直哉的文学创作技巧,并于昭和27年(1952)写下了长篇小说《春城》,反映了大学生出身的海军预备役士兵在战争时期如何经历恋爱体验和海军体验,如何对待战火中的青春等,从主人公面对众多的死亡所表现出的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作者的一份批判精神,由此该小说获得了该年度的“读卖文学奖”。在创作主题上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表现家庭关系和生活琐事的作品以外,也有部分涉及战争,表现厌战情绪的作品,如安冈的《遁走》(1956)、阿川的《云的墓标》(1956)等;还有抵制美国占领军,反对日本人盲目追随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作品,如小岛的《美国人的学校》、曾野的《远方来客》、远藤周作的《海与毒药》(1957)等;更有反映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作品,如阿川的《魔鬼的遗产》(1954)等等。正是这样的“百花齐放”才使得“第三新人”独具魅力,也正是这样的“百花齐放”才成就了战后“私小说”、“心境小说”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尽管“第三新人”们不注重社会现实中的大问题,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关心现实社会,逃避现实。他们在继承传统“私小说”的手法上还有很大的创新。首先,很多作家都能立足于现代社会的视野,力图扩展小说的主题,或反映当今社会的家庭危机、或表现性意识的觉醒与性心理危机、或展现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或描写美国占领军的恶行。他们试图根据自身的各种体验,从日常家庭生活中反映个体的内心世界,再将自我的内心感受折射到战后的现实社会。这就多少弥补了一点传统“私小说”缺乏社会性的内容,同时将社会化的“自我”融入作品中。安冈在《论志贺直哉》(1967)中就这样明确表示:如果说“我”的社会化,不如说社会化的“我”更恰当。社会是个人造出来的观念,但是社会造不出一个活人。甚至连一个蝼蚁也造不出(23)。其次,“第三新人”的部分作家有意识地将独特的抽象性、象征性、心理主义等手法运用到传统“私小说”的创作中,从而扩大了传统“私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例如小岛信夫在文学创作中常常会运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他喜欢果戈理、卡夫卡的作品,对寓言和象征较感兴趣,因此在《在火车上》(1948)、《美国人的学校》、《岛》(1956)、《拥抱家族》等反映日本被占领时代的小说里不断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象征性、抽象性的画卷。在作品中,他将心理主义纳入小说的世界,尽量采用综合性手法表现日本人对战前日本道德观的抛弃、对战后美国化的追求的形象,以展示战后日本的真实面貌。他认为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喜欢“私小说”的特定世界。他曾撰文这样说:
我们之所以对“私小说”不够满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私小说”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加以抽象,由此确定了我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个体的我。我就处在了一个核心的地位。(24)
显然,他代表部分“第三新人”表达了对传统“私小说”创作的不满,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扩展传统“私小说”的创作手法。无独有偶,像吉行淳之介在其《骤雨》、《娼妇的房间》、《鸟兽虫鱼》(1959)等作品中也采用抽象性和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来把握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指主人公的心境或内心世界)交叉变化的现实。此外,还有远藤周作、曾野绫子等人运用大量的象征性和心理主义等手法表现外来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浸润,从中探寻日本精神的根脉。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影、视、剧业的兴隆,商品性的文学作品以及对旧文坛反叛的作家开始大量涌现。像描写无目标、无理想、生活放荡不羁又充满好斗、狂躁不安的“太阳族”文学的石原慎太郎(1932— )在新闻宣传媒介的大肆宣传和鼓动下,以《太阳的季节》(1955)不仅荣获了1955年下半年度的“芥川文学奖”,而且一夜之间便成为反叛文学的一颗耀眼的新星。随之,开高健(1930—1989)以描写批判社会普通观念和价值观的小说《皇帝的新衣》(1957)一举获得1957年下半年的“芥川文学奖”,紧接着大江健三郎(1935— )又以描写美国占领军与当地村民之间发生的牧歌式、悲剧式的故事——《饲育》(1958)于作品完成当年的上半年获得“芥川文学奖”。以上述三人为代表的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战后青年一代为探索人生道路而陷入虚无和不安的苦恼中,表现了年轻人生活在物质世界达到丰富的现实社会里,精神世界是一片空虚。他们在创作上有别于“第三新人”,有意识地开始把探索个人的内心世界、追求自我的真实性转向了社会问题。至此,现代日本文坛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文学交替,“第三新人”也就此完成了其“填补坑坑洼洼道路”(25)的历史使命。
总之,“第三新人”是战后日本文坛努力回归传统“私小说”的作家群。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私小说”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努力创新了“私小说”的传统,使“私小说”文学在战后文坛得以进一步向前发展。他们为战后日本文坛弘扬传统文学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
(1) 转引自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2) 佐藤胜、古林尚:《现代文学史·战后的文学》,东京:有斐阁选书,1978年版,第2页。
(3) 卞崇道:《二十世纪日本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个别地方有改动。
(4)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5) 矶田光一、楠本宪吉、中村光夫等主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增补改订),东京:新潮社,1991年版,第1342页。
(6) 小田切秀雄:《讲座日本文学史》(第1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152页。
(7) 三好行雄·浅井清主编:《近代日本文学小辞典》,东京:有斐阁,1981年版,第278页。
(8)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
(9) 犬养廉、神保五弥、浅井清主编:《详解日本文学史》,东京:桐原书店,1987年,第183页。
(10) 《现代文艺评论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95),东京:筑摩书房,1958年版,第222页。
(11) 小林秀雄:《小林秀雄初期文艺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378—401页。
(12) 矶田光一、楠本宪吉、中村光夫等主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增补改订),东京:新潮社,1991年版,第1343页。
(13)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14) 所谓“芥川文学奖”是以“新思潮”派杰出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命名的,为了纪念他并表彰他的突出业绩,由该文学派著名作家菊池宽(1888—1948)提议于昭和10年(1935)设定奖励文学新人的“纯文学奖”。每年春秋季节各选评一回。该奖项被视为新人作家登上日本文坛的门径。
(15)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
(16) 服部达撰写的论文标题为“劣等生、小残废者、市民——从第三新人到第四新人”。
(17) 松原新一、矶田光一、秋山骏:《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改定增补),东京:讲谈社,1979年版,第200页。
(18) 松原新一、矶田光一、秋山骏:《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改定增补),东京:讲谈社,1979年版,第199页。
(19)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123页。
(20) 同上,第123页。
(21)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123页。
(22) 同上,第124页。
(23) 转引自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24) 松原新一、矶田光一、秋山骏:《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改定增补),东京:讲谈社,1979年版,第222页。该文章题为“《岛》——具有抽象倾向的文学”,收于《小岛信夫文学论集》(1966)。
(25) 安冈章太郎认为:“战后派的人们勇敢地完成了压路机的开路任务,路是有了,但坑坑洼洼不平。我就填补这些坑坑洼洼。”(转引自王长新:《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这种填补坑洼的工作几乎成了“第三新人”的责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